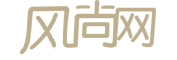南澳葡萄酒 更进一杯又何妨
南澳是重要的新世界葡萄酒产地。和大部分盛产葡萄酒的地方纬度相反,这里在每年5月左右就可以喝到“新酒”,堪称全世界每年上市最早的葡萄酒。近来,本地人纷纷爱上了那些年龄只有一两年的葡萄酒。驱车前往小型私人酒庄(Boutique Winery)品尝当年新酒、享用午餐俨然已成风尚。
一个在墨尔本长大的朋友曾向我讲述100多年前澳洲Swag Man的故事,听起来就是那个时期的背包客:一些身强体壮的年轻人,步行穿越这个国家,原因不得而知但不难猜测。沿途有很多酒庄方便他们停留打工。他们的帽子有一圈古怪的帽檐,上面挂着葡萄酒瓶的软木塞,晃动时可以赶走乡下讨厌的牛蝇。在这个故事中,软木塞唾手可得的程度让人惊奇,而葡萄酒庄就是一个个液体补给的驿站。
如今,沿着一号高速公路一直开,就能环绕整个澳大利亚,且没有任何收费站阻隔,这样的便利让私人酒庄没理由不成为周末迷你假日的首选。
“我喜欢红酒。因为它更复杂、更神秘,让我的身体发生反应。”身材略微有些发福的Ralph如是回答我这个入门者关于“爱红酒还是白酒”的问题。答案如我所想。
Ralph在南澳经营一个小型旅游公司“杯酒人生”(Life is a cabinet),那时我们一行人正站在阿德莱德山(Adelaide hill)的半山腰停车歇息。众人目光能及的谷地,是著名的“冷性气候酒”出产地Hahndorf镇。这里以生产上好的夏敦埃酒(白葡萄酒的一种)出名。
Hahndorf镇是南澳著名的德国镇,居民几乎都是德国后裔。1840年,一批信仰路德宗的德国人,为了躲避宗教迫害,从南非过境来到这里定居。他们不仅带来了棕榈树,还带来了葡萄树的种子。
Ralph自己也有一半德国血统,他的母亲是德国人,父亲是波西尼亚人。1970年代,大批欧洲人在“移民或灭绝”(populate or perish)的口号鼓动下千里迢迢来此时,他已是个小有名气的电视剧演员。他先领我们去HHW,这是一对男同性恋人经营的酒庄。

爱人同志和玫瑰红酒
HHW位于只有一条主街的Hahndorf镇的尽头。当我们找到它的时候,他家两只酒犬(Wine Dog)顶着油亮油亮的毛发欢欣鼓舞地奔了过来。 这是一对明星酒犬,曾上过Wine Dogs杂志。它们的专职是庆祝每年的葡萄丰收,兼会替品酒的人看管那些容易发生意外的顽皮小孩。
这对恋人和当地一位已故画家曾经是好友,画家的一幅作品被当作标识印在HHW每瓶酒上。那是一棵如烟的树。店堂一角插缀着去年圣诞节欢庆用的柏树枝,上面挂满了这一年来写着祝福的小卡片。
Mark是恋人之一。他手势轻快,举着盛酒的玻璃杯向我们推荐一种夏敦埃酒,名叫White Mischief。这种酒色如香槟,不是在橡木桶里酿制,而是在金属铁罐里孕育成熟,因此更加冰冷甘冽,同时清脆愉快、内容丰富。此酒用白索维农和灰比诺(Sauvignon Blancs,Pinot Gris,都是葡萄品种)混和酿成。前者酸味很浓,闻起来有种甜瓜的味道,如果在气候更冷的地方栽种,则容易发出草本的香味。后者是对生长气候特别挑剔的灰比诺,它的嫡亲――黑比诺(Pinot Nior)是酿制顶级玫瑰红酒的原料,皮薄得惊人。
比诺对气候的要求太高,即便全程用心呵护也未见得能画上完美的句号。电影《杯酒人生》里的Miles做着遥不可及的作家梦时,就总是念叨着他最心仪和能令他顾影自怜的Pinot。Pinot Noir经常会有一种黑樱桃的味道,渐渐上升为草莓和丁香的气味,质地如丝绸。
对于那些喜欢白葡萄酒的人如我,在“有颜色的酒”中,更倾向于对玫瑰红酒(Rosé)产生好感。这种酒配海鲜、泰国菜、咖喱都口感良好,和白葡萄酒一样需要冷藏后饮用。事实上,它也是红葡萄酿成的,只是装桶之后去了皮。介于香槟色和红酒色之间的玫瑰色泽是去皮之前浸泡一小段时间造成的。 相比那些产于法国、意大利的旧世界葡萄酒,澳洲的酒更具新鲜馥郁的花果香气。“很平衡的口感,成熟的甜浆果味道。入口如泉水般润泽,尾调稍干。”《悉尼早报》(Sydney Morning Herald)的Huon Hooke曾这样评价这里的Rosé2004。我觉得隐约有些蜂蜜的味道。2002 Chardonna发育成熟、正当时节,被当地美酒杂志Winestate评为南澳最好的夏敦埃酒之一。
坐在修葺一新的露台上品尝美酒和产于阿德莱德山区的美食,心情骤然明快起来。临桌一对中年爱人正在互诉衷肠,女人满脸羞涩。

工业时代的酒庄
在除了南澳以外的其它州,酒馆里人声鼎沸的时候很容易听到这般对外国人滑稽的吹嘘:“我爷爷的爷爷只是因为偷了一小块面包,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这样我才来到了这个天堂般的地方!”南澳是澳大利亚唯一没有流放犯的州。让这里的人们引为自豪的是“非囚犯的后代”,以及驿站般的酒庄。
相比较大部分装饰得如同家庭旅馆的酒庄,SHAW AND SMITH似乎是在一片牧歌式的温文尔雅中加了点重金属摇滚。 Martin Shaw和Michael Hill Smith这对表兄弟在1989年开了这个酒庄,坚持使用阿德莱德山一带的葡萄酿酒,但是赋以更多的当代含义。他们在1994年和1999年各种植了一批葡萄,2000年造了新厂房,2002年又更新了灌装线。一溜金属色厂房,在碧绿草地和湛蓝天空下显得酷味十足。
中国的一些葡萄酒厂过于模仿法国波尔多一带的葡萄酒口味,以至很多人认为在法国品酒就是认祖归宗。而在这一带的品酒经历更像是一场奇遇,味蕾总有惊喜。
我们在试酒屋里遇到了Katie。她有一半亚洲血统,母亲是马来西亚人。她向我们介绍芝士如何与酒搭配,以调动两者的最佳风味。例如山羊乳干酪应该配白索维农酒,格里尔干奶酪配红酒味道更佳。这个褐色皮肤的女孩在阿德莱德大学主攻酿酒专业,课程中既有对味蕾灵敏度要求极高的“品酒学”,又有工程类的“自动化控制学”,认为温度、时间的控制对于葡萄酒香味起着重要的作用,当然还有当年的气候。SHAW AND SMITH对于品质的控制使其生产的葡萄酒能远销国外,香港半岛酒店的酒窖也陈列了他们的酒。
事实上就连Katie也不得不承认这点:我们遇到的每一瓶葡萄酒的香气,除了天气、温度、时间长短,还由各种说不上来的神秘因素决定。她还说起狄奥尼索斯,那个古希腊色雷斯人的葡萄酒之神。酒神所主导的狂欢,乃是秘密的宗教仪式。

百岁葡萄藤,以及一群路德教徒后裔
那些种在葡萄园旁的玫瑰充当了试验者,它们的存在是为了能及时反应附近葡萄树的虫害情况。因为玫瑰很脆弱,对病虫害更敏感。
不知是否因为Langmell酒庄的玫瑰们更有奉献精神,这里最远古的葡萄藤已经活到163岁。令人惊奇的是,它们仍能产出上好的葡萄酒,而法国那些同样年纪或更年长的葡萄藤早已为瘤蚜所毁。澳洲这片崭新的大陆,反倒成为世界上最古老葡萄藤的所在地。
Seppelt家族1851年从德国移民至巴萝沙山谷,他们家生产的起泡酒、佐餐酒和加烈葡萄酒最有风味。酒庄的一款加烈酒Seppelt Rare DP90曾获奖无数。他们的先人是 “凡信徒皆可为祭司,无须各级神职人员为中介”的路德教徒。 歌德说“酒使人心愉悦,而欢愉正是所有美德之母……我继续与葡萄酒作精神上的对话,它们使我产生伟大的思想,使我创造出美妙的事物。”Seppelt姓氏的后裔们在此定居,建造有着精致雕梁的酒厂,为每一个橡木桶内的琼浆作观察记录,细心打理那些盘根错节的葡萄藤,在橱窗里摆上涂着金黄色染料的松果和先辈的黑白照片――势将“精神上的对话”连绵到底。
巴萝沙山谷一带的酒庄难以计数,从高空俯看更能说明问题。Kies一家在这里经营直升飞机旅游公司,老Kies将自己只有21岁的女儿Billie-Jo培养成澳洲历史上年纪最小的直升飞机驾驶员。在Billie的眼里,从离地面300多米的地方看巴萝沙,没有山谷,只有满目翠绿的葡萄园。
后来,在尖峰石镇一块状如修女的石灰岩旁边,我们打开“第五条腿”(the fifth leg,一种葡萄酒的品牌名)的Shiraz和Riesling。我和另一个女孩研究着标签上那只表情古怪的小狗,一群人喝酒嬉笑,等着印度洋上璀璨的日落。 越野车里放着年轻的英国女爵士歌手Katie Melua的新专辑。我得说,她年纪太小,声音虽有磁力却脆生生,不太像个唱爵士的,却早在那首“北京有九百万辆自行车(there are nine million bicycles in Beijing)”的时候就让我喜欢。这样的嗓音,有点像当年的葡萄酒:入口容易,浑然不觉时已更进一杯,于是不知晓便能让人醉。

- 上一篇:上一篇:用性感鸡尾酒挥霍非常夏日
- 下一篇:下一篇:改变葡萄酒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