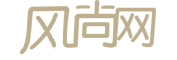周有光 105岁从世界看中国
时间:2010-08-11 01:04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照片背面,是沈从文写的“张家二姐作新娘,从文”
眼前的小书桌,黄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眉毛已经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我这种从外国回来的人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了。”待在桌前坐定,他摘下眼镜,合上书,将台灯推开些,戴上助听器,手不抖,气不喘。“我们要讲老实话,你们记录的时候,有些话少记录一点好了。”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照片背面,是沈从文写的“张家二姐作新娘,从文”
眼前的小书桌,黄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眉毛已经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我这种从外国回来的人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了。”待在桌前坐定,他摘下眼镜,合上书,将台灯推开些,戴上助听器,手不抖,气不喘。“我们要讲老实话,你们记录的时候,有些话少记录一点好了。”
 晚年的周有光与张允和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5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揸开,很认真。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还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当年他推行简体字,现在却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他完全有资格跟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4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4个月,林彪死了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文革’就没有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跟50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他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在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
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93”这个数字,画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张允和的自述文集《曲终人不散》,送给记者,署“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100多岁的长者,常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
人物周刊: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人家对我们的恋爱很感兴趣,可是我的兴趣在学问上面,不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的老伴儿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3个阶段。苏州阶段,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就到外国去了。
沈从文跟三妹(张兆和)的恋爱是另一种。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讲讲?三妹气得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从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来。他们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一点不用追,我跟老伴儿是流水式的,他是冲击性的。
人物周刊:据说您给张允和先生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是真的吗?
周有光:对。他们家太有钱了!我们家也是大家,但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掉了。那时我很穷,我说我害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在杭州很有趣味,礼拜天去玩,不能手牵手,走路还要离开一段。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们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故意听我们讲话。后来,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他坐在我们旁边,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我说来了3年了。他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我的老伴儿鼻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他以为她是外国人!
人物周刊:您觉得金钱对婚姻重要吗?
周有光:可以说重要也可以说不重要。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的,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能没有钱。有许多人为了钱结婚,也有人为了钱闹离婚,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我主张恋爱不仅要爱,还要有敬。许多人离婚是因为对对方没有敬重的心。我们两个人吃咖啡、喝茶,都是举杯齐眉,表示敬重。既有爱又有敬,婚姻会比较圆满。我跟我老伴儿,结婚70年,美满70年。我一个孙女在美国,买周年礼给我们,发现印好的卡片就到60年,没有70年的。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哇啦哇啦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对什么事都是乐观态度,加上我既要爱又要敬的婚姻观,我们很幸福。
要以世界视角看中国
人物周刊:您曾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三期:原始(形意)文字时期,古典(意音)时期和字母(表音)时期,汉字在宏观分期中处于古典时期。这3个历史时期是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轨迹?您曾说要让汉字字母化“等五百年吧”,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字母化是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周有光:人类文字发展分几个阶段,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样,我比较了几十种看法之后,把它分3个阶段,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原始文字是不成熟的,它不能全部记下我们想说的,尤其是虚指,有些部分要靠你自己记。汉字是古典文字,重要的古典文字还有两河流域的楔形字、古埃及的象形字和美洲的玛雅文。玛雅文一度失传了,差不多600年没有人认识,后来一个俄罗斯人把它认出来了。我在1956年搞到了俄罗斯的资料,第一个把它介绍过来。可是几年之前举行大规模的玛雅文化展览,只有玛雅文没有玛雅文解释,他们不知道玛雅文已经看得懂了!
古典文字作为符号是很难认的,之后有了字母文字,这是高度思维的结果,也是发展趋势。在咱们国家,有人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拼音化有两个含义:广义的拼音化,比如用拼音发短信、给汉字注音,方便了很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觉得汉字很难。80年代到欧美去讲学,有个教授问我,你们汉字有没有1000个?他以为1000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7000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的文字,这个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写,还要你能看懂,100年后的人能看懂。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你等500年吧!
人物周刊:您曾举文艺复兴的例子旁证对“华夏文化”应该“温故而知新”,对古代文化的精华加以提高和发展,再创造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怎么看?
周有光: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孔夫子是谨慎,说不要创造,其实他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
人物周刊:除了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周有光:我是学经济出身,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领导让我做文字改革,我就改行了。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所以我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当时发行量很大,日本很快就翻译过去了。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
前两天我看到这本《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一点,出版社说写得太心急了,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了。说真的,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
文化不分国家。但我们这里,《人民日报》好多文章还是老一套,现在大学政治课都是老师讲给天花板听。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老一套的宣传迟早要改掉的。
我们很多社会科学处于玄学阶段
人物周刊:您曾提及历史发展的轨道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从听任自然到改造自然;在政治方面,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在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您这个轨道的设想是怎么产生的?
周有光:社会的发展可以从好多角度看,主要是3个: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经济方面有3个高峰: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中国农业化发展特别好,值得骄傲;工业化我们落后了,现在靠引进外包经济慢慢好起来,但这是初级阶段;信息化我们也进入了,比较快,特别是手机。但也在低阶段,最近不是正跟谷歌吵架吗,就是信息化的问题。
政治是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民主制度3000多年前古希腊就有了,可美国发展得比别的地方快。欧洲传统势力大,有很强大的特权阶级。我常说贪污很简单的,有特权有保密权,当然可以贪污,一民主特权没用处了,所以许多人要反对民主。
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人家问我,你105岁,还能写文章,有什么长寿之道?我说没有,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这就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是推理性的,譬如我们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推出地球绕着太阳转;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人物周刊:您觉得当下中国处于什么阶段?
周有光:民主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在美国多了两样东西:第一是电视辩论。美国选举总统要在电视上面辩论。这两天新闻说,英国这个最早开创民主的国家一直没有电视辩论,也宣布今年首相大选要开始电视辩论了;第二是国际观察。他在国际上有3个重要的观察团,谁选举他就派人来看,看了也不讲话,回去之后才讲话,把你这个选举的真假看得很清楚。我们的选举,我这个老头子不能出去,什么人代替我选、选什么人,我都不知道。
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改了很多了,全部都改是不可能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民主,这是自然趋势。当然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但利多一点。很多人问为什么欧洲帝国主义垮台了而美帝国主义没有。有人说美国条件好,有两个洋保护它,那南美洲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很糟糕?关键是美国有民主。
欧洲国家垮在殖民地上,美国用技术创新代替殖民,用许多新方法赚你的钱,你还要感激它。最近《阿凡达》这么火,他们要给我买票,买不到。北京人家里几十样电器,90%都是美国的。最近我们跟美国吵,不行,吵不过它。全世界的网络有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它控制全世界的网络,怎么跟它打仗呢?美国花了3天时间切断萨达姆的通讯系统,不到一个礼拜美国坦克就开到了巴格达城里。所以不能用老办法对付它。怎么对付它?要研究!它最怕我们的科技进步!
我们的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用的是科学思维,但我们的社会科学还很不发达,自己限制自己,有很多处于玄学思维阶段。有一次《群言》杂志开座谈会,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讲,他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女儿跟着回来读中学。老师让她说读完《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什么感想,她说资本主义不好,害得这个孩子很苦,社会主义要注意不要这样做。老师批她一个零分。他朋友就去找老师。老师说,你怎么这么教孩子,要告诉孩子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坏事的!家长说,这不是叫她讲假话吗?老师回答,这不叫假话,叫思想引导!
这显然是玄学思想,不是科学思想。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很多思想没有引进来。比如没有引进教育学,教育搞得很糟糕。许多社会规律在我们这里都不起作用。
整个来讲我们还在第二阶段。我们是在前进,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一点是很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假如这样,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
晚年的周有光与张允和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5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揸开,很认真。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还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当年他推行简体字,现在却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他完全有资格跟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4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4个月,林彪死了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文革’就没有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跟50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他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在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
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93”这个数字,画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张允和的自述文集《曲终人不散》,送给记者,署“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100多岁的长者,常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
人物周刊: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人家对我们的恋爱很感兴趣,可是我的兴趣在学问上面,不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的老伴儿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3个阶段。苏州阶段,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就到外国去了。
沈从文跟三妹(张兆和)的恋爱是另一种。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讲讲?三妹气得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从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来。他们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一点不用追,我跟老伴儿是流水式的,他是冲击性的。
人物周刊:据说您给张允和先生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是真的吗?
周有光:对。他们家太有钱了!我们家也是大家,但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掉了。那时我很穷,我说我害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在杭州很有趣味,礼拜天去玩,不能手牵手,走路还要离开一段。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们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故意听我们讲话。后来,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他坐在我们旁边,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我说来了3年了。他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我的老伴儿鼻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他以为她是外国人!
人物周刊:您觉得金钱对婚姻重要吗?
周有光:可以说重要也可以说不重要。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的,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能没有钱。有许多人为了钱结婚,也有人为了钱闹离婚,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我主张恋爱不仅要爱,还要有敬。许多人离婚是因为对对方没有敬重的心。我们两个人吃咖啡、喝茶,都是举杯齐眉,表示敬重。既有爱又有敬,婚姻会比较圆满。我跟我老伴儿,结婚70年,美满70年。我一个孙女在美国,买周年礼给我们,发现印好的卡片就到60年,没有70年的。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哇啦哇啦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对什么事都是乐观态度,加上我既要爱又要敬的婚姻观,我们很幸福。
要以世界视角看中国
人物周刊:您曾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三期:原始(形意)文字时期,古典(意音)时期和字母(表音)时期,汉字在宏观分期中处于古典时期。这3个历史时期是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轨迹?您曾说要让汉字字母化“等五百年吧”,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字母化是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周有光:人类文字发展分几个阶段,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样,我比较了几十种看法之后,把它分3个阶段,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原始文字是不成熟的,它不能全部记下我们想说的,尤其是虚指,有些部分要靠你自己记。汉字是古典文字,重要的古典文字还有两河流域的楔形字、古埃及的象形字和美洲的玛雅文。玛雅文一度失传了,差不多600年没有人认识,后来一个俄罗斯人把它认出来了。我在1956年搞到了俄罗斯的资料,第一个把它介绍过来。可是几年之前举行大规模的玛雅文化展览,只有玛雅文没有玛雅文解释,他们不知道玛雅文已经看得懂了!
古典文字作为符号是很难认的,之后有了字母文字,这是高度思维的结果,也是发展趋势。在咱们国家,有人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拼音化有两个含义:广义的拼音化,比如用拼音发短信、给汉字注音,方便了很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觉得汉字很难。80年代到欧美去讲学,有个教授问我,你们汉字有没有1000个?他以为1000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7000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的文字,这个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写,还要你能看懂,100年后的人能看懂。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你等500年吧!
人物周刊:您曾举文艺复兴的例子旁证对“华夏文化”应该“温故而知新”,对古代文化的精华加以提高和发展,再创造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怎么看?
周有光: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孔夫子是谨慎,说不要创造,其实他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
人物周刊:除了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周有光:我是学经济出身,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领导让我做文字改革,我就改行了。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所以我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当时发行量很大,日本很快就翻译过去了。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
前两天我看到这本《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一点,出版社说写得太心急了,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了。说真的,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
文化不分国家。但我们这里,《人民日报》好多文章还是老一套,现在大学政治课都是老师讲给天花板听。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老一套的宣传迟早要改掉的。
我们很多社会科学处于玄学阶段
人物周刊:您曾提及历史发展的轨道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从听任自然到改造自然;在政治方面,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在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您这个轨道的设想是怎么产生的?
周有光:社会的发展可以从好多角度看,主要是3个: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经济方面有3个高峰: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中国农业化发展特别好,值得骄傲;工业化我们落后了,现在靠引进外包经济慢慢好起来,但这是初级阶段;信息化我们也进入了,比较快,特别是手机。但也在低阶段,最近不是正跟谷歌吵架吗,就是信息化的问题。
政治是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民主制度3000多年前古希腊就有了,可美国发展得比别的地方快。欧洲传统势力大,有很强大的特权阶级。我常说贪污很简单的,有特权有保密权,当然可以贪污,一民主特权没用处了,所以许多人要反对民主。
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人家问我,你105岁,还能写文章,有什么长寿之道?我说没有,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这就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是推理性的,譬如我们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推出地球绕着太阳转;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人物周刊:您觉得当下中国处于什么阶段?
周有光:民主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在美国多了两样东西:第一是电视辩论。美国选举总统要在电视上面辩论。这两天新闻说,英国这个最早开创民主的国家一直没有电视辩论,也宣布今年首相大选要开始电视辩论了;第二是国际观察。他在国际上有3个重要的观察团,谁选举他就派人来看,看了也不讲话,回去之后才讲话,把你这个选举的真假看得很清楚。我们的选举,我这个老头子不能出去,什么人代替我选、选什么人,我都不知道。
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改了很多了,全部都改是不可能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民主,这是自然趋势。当然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但利多一点。很多人问为什么欧洲帝国主义垮台了而美帝国主义没有。有人说美国条件好,有两个洋保护它,那南美洲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很糟糕?关键是美国有民主。
欧洲国家垮在殖民地上,美国用技术创新代替殖民,用许多新方法赚你的钱,你还要感激它。最近《阿凡达》这么火,他们要给我买票,买不到。北京人家里几十样电器,90%都是美国的。最近我们跟美国吵,不行,吵不过它。全世界的网络有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它控制全世界的网络,怎么跟它打仗呢?美国花了3天时间切断萨达姆的通讯系统,不到一个礼拜美国坦克就开到了巴格达城里。所以不能用老办法对付它。怎么对付它?要研究!它最怕我们的科技进步!
我们的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用的是科学思维,但我们的社会科学还很不发达,自己限制自己,有很多处于玄学思维阶段。有一次《群言》杂志开座谈会,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讲,他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女儿跟着回来读中学。老师让她说读完《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什么感想,她说资本主义不好,害得这个孩子很苦,社会主义要注意不要这样做。老师批她一个零分。他朋友就去找老师。老师说,你怎么这么教孩子,要告诉孩子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坏事的!家长说,这不是叫她讲假话吗?老师回答,这不叫假话,叫思想引导!
这显然是玄学思想,不是科学思想。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很多思想没有引进来。比如没有引进教育学,教育搞得很糟糕。许多社会规律在我们这里都不起作用。
整个来讲我们还在第二阶段。我们是在前进,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一点是很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假如这样,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照片背面,是沈从文写的“张家二姐作新娘,从文”
眼前的小书桌,黄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眉毛已经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我这种从外国回来的人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了。”待在桌前坐定,他摘下眼镜,合上书,将台灯推开些,戴上助听器,手不抖,气不喘。“我们要讲老实话,你们记录的时候,有些话少记录一点好了。”
1933年4月30日周有光与张允和结婚,照片背面,是沈从文写的“张家二姐作新娘,从文”
眼前的小书桌,黄色的漆掉了大半,露出木头纹理,但磨得久了,也不觉得粗糙。眉毛已经全然没有,两道眉骨泛着红润的光,105岁的周有光老人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讲笑话,他说:“很有趣味。”一笑就用手挡在嘴前,好像不该笑得这么开心似的。“人老了,牙不大好。”他调皮地说,“我不讲究吃,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
“资本主义是腐朽的,我这种从外国回来的人腐朽思想是很多的,你们听我讲话要小心了。”待在桌前坐定,他摘下眼镜,合上书,将台灯推开些,戴上助听器,手不抖,气不喘。“我们要讲老实话,你们记录的时候,有些话少记录一点好了。”
 晚年的周有光与张允和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5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揸开,很认真。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还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当年他推行简体字,现在却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他完全有资格跟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4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4个月,林彪死了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文革’就没有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跟50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他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在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
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93”这个数字,画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张允和的自述文集《曲终人不散》,送给记者,署“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100多岁的长者,常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
人物周刊: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人家对我们的恋爱很感兴趣,可是我的兴趣在学问上面,不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的老伴儿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3个阶段。苏州阶段,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就到外国去了。
沈从文跟三妹(张兆和)的恋爱是另一种。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讲讲?三妹气得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从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来。他们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一点不用追,我跟老伴儿是流水式的,他是冲击性的。
人物周刊:据说您给张允和先生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是真的吗?
周有光:对。他们家太有钱了!我们家也是大家,但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掉了。那时我很穷,我说我害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在杭州很有趣味,礼拜天去玩,不能手牵手,走路还要离开一段。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们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故意听我们讲话。后来,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他坐在我们旁边,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我说来了3年了。他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我的老伴儿鼻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他以为她是外国人!
人物周刊:您觉得金钱对婚姻重要吗?
周有光:可以说重要也可以说不重要。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的,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能没有钱。有许多人为了钱结婚,也有人为了钱闹离婚,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我主张恋爱不仅要爱,还要有敬。许多人离婚是因为对对方没有敬重的心。我们两个人吃咖啡、喝茶,都是举杯齐眉,表示敬重。既有爱又有敬,婚姻会比较圆满。我跟我老伴儿,结婚70年,美满70年。我一个孙女在美国,买周年礼给我们,发现印好的卡片就到60年,没有70年的。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哇啦哇啦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对什么事都是乐观态度,加上我既要爱又要敬的婚姻观,我们很幸福。
要以世界视角看中国
人物周刊:您曾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三期:原始(形意)文字时期,古典(意音)时期和字母(表音)时期,汉字在宏观分期中处于古典时期。这3个历史时期是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轨迹?您曾说要让汉字字母化“等五百年吧”,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字母化是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周有光:人类文字发展分几个阶段,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样,我比较了几十种看法之后,把它分3个阶段,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原始文字是不成熟的,它不能全部记下我们想说的,尤其是虚指,有些部分要靠你自己记。汉字是古典文字,重要的古典文字还有两河流域的楔形字、古埃及的象形字和美洲的玛雅文。玛雅文一度失传了,差不多600年没有人认识,后来一个俄罗斯人把它认出来了。我在1956年搞到了俄罗斯的资料,第一个把它介绍过来。可是几年之前举行大规模的玛雅文化展览,只有玛雅文没有玛雅文解释,他们不知道玛雅文已经看得懂了!
古典文字作为符号是很难认的,之后有了字母文字,这是高度思维的结果,也是发展趋势。在咱们国家,有人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拼音化有两个含义:广义的拼音化,比如用拼音发短信、给汉字注音,方便了很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觉得汉字很难。80年代到欧美去讲学,有个教授问我,你们汉字有没有1000个?他以为1000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7000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的文字,这个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写,还要你能看懂,100年后的人能看懂。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你等500年吧!
人物周刊:您曾举文艺复兴的例子旁证对“华夏文化”应该“温故而知新”,对古代文化的精华加以提高和发展,再创造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怎么看?
周有光: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孔夫子是谨慎,说不要创造,其实他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
人物周刊:除了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周有光:我是学经济出身,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领导让我做文字改革,我就改行了。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所以我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当时发行量很大,日本很快就翻译过去了。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
前两天我看到这本《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一点,出版社说写得太心急了,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了。说真的,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
文化不分国家。但我们这里,《人民日报》好多文章还是老一套,现在大学政治课都是老师讲给天花板听。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老一套的宣传迟早要改掉的。
我们很多社会科学处于玄学阶段
人物周刊:您曾提及历史发展的轨道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从听任自然到改造自然;在政治方面,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在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您这个轨道的设想是怎么产生的?
周有光:社会的发展可以从好多角度看,主要是3个: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经济方面有3个高峰: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中国农业化发展特别好,值得骄傲;工业化我们落后了,现在靠引进外包经济慢慢好起来,但这是初级阶段;信息化我们也进入了,比较快,特别是手机。但也在低阶段,最近不是正跟谷歌吵架吗,就是信息化的问题。
政治是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民主制度3000多年前古希腊就有了,可美国发展得比别的地方快。欧洲传统势力大,有很强大的特权阶级。我常说贪污很简单的,有特权有保密权,当然可以贪污,一民主特权没用处了,所以许多人要反对民主。
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人家问我,你105岁,还能写文章,有什么长寿之道?我说没有,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这就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是推理性的,譬如我们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推出地球绕着太阳转;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人物周刊:您觉得当下中国处于什么阶段?
周有光:民主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在美国多了两样东西:第一是电视辩论。美国选举总统要在电视上面辩论。这两天新闻说,英国这个最早开创民主的国家一直没有电视辩论,也宣布今年首相大选要开始电视辩论了;第二是国际观察。他在国际上有3个重要的观察团,谁选举他就派人来看,看了也不讲话,回去之后才讲话,把你这个选举的真假看得很清楚。我们的选举,我这个老头子不能出去,什么人代替我选、选什么人,我都不知道。
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改了很多了,全部都改是不可能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民主,这是自然趋势。当然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但利多一点。很多人问为什么欧洲帝国主义垮台了而美帝国主义没有。有人说美国条件好,有两个洋保护它,那南美洲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很糟糕?关键是美国有民主。
欧洲国家垮在殖民地上,美国用技术创新代替殖民,用许多新方法赚你的钱,你还要感激它。最近《阿凡达》这么火,他们要给我买票,买不到。北京人家里几十样电器,90%都是美国的。最近我们跟美国吵,不行,吵不过它。全世界的网络有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它控制全世界的网络,怎么跟它打仗呢?美国花了3天时间切断萨达姆的通讯系统,不到一个礼拜美国坦克就开到了巴格达城里。所以不能用老办法对付它。怎么对付它?要研究!它最怕我们的科技进步!
我们的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用的是科学思维,但我们的社会科学还很不发达,自己限制自己,有很多处于玄学思维阶段。有一次《群言》杂志开座谈会,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讲,他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女儿跟着回来读中学。老师让她说读完《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什么感想,她说资本主义不好,害得这个孩子很苦,社会主义要注意不要这样做。老师批她一个零分。他朋友就去找老师。老师说,你怎么这么教孩子,要告诉孩子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坏事的!家长说,这不是叫她讲假话吗?老师回答,这不叫假话,叫思想引导!
这显然是玄学思想,不是科学思想。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很多思想没有引进来。比如没有引进教育学,教育搞得很糟糕。许多社会规律在我们这里都不起作用。
整个来讲我们还在第二阶段。我们是在前进,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一点是很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假如这样,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
晚年的周有光与张允和
“我计算过,用电脑写文章之后,我的收入增加5倍。”他举着一只手,手指揸开,很认真。105岁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脚步。他知道“谷歌”的纠纷,还差点去看了《阿凡达》;我们用惯电脑,“提笔忘字”,他也会忘;当年他推行简体字,现在却经常忘记简体字怎么写,记得英文怎么说,却记不得中文怎么说。他完全有资格跟记者讲古:“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从留辫子到剪发;看着家里面从原来点洋灯变成点电灯,用上了电脑;还有手机,万里之外的人跑到耳朵旁边了。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
1956年,周有光刚从上海来到北京,住在沙滩,外面大雨里面小雨,他自己写了个《新陋室铭》,“房间阴暗,更显得窗子明亮。书桌不平,更怪我伏案太勤。门槛破烂,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欢迎老友来临。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作菜橱,菜有书香。”
改革开放后,换到朝内大街后拐棒胡同,不大的面积被分成4间,已经是特别优待。“后来单位在方庄买了比较好的房子,叫我搬走。我说年纪大了,不活动了,小一点无所谓,半张破桌子、半间小屋子,我不要好的了。我老了,再好也没有意思。再说我是过过好生活的人,不在乎这个。”
“文革”时,下放到宁夏,“大家以为不会回来了,很多人心情很坏,我觉得很好,不是下放这种地方我怎么会来?都不知道中国还有这种地方。过了两年4个月,林彪死了又回来了。所以我不发愁,发愁没有用处。我遇到过许多困难,已经有经验了,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不要慌。”他又半掩着嘴笑了,很自得。他的《汉字改革概论》发行量很大,但“50年代有稿费的,'文革’就没有了,我好多书都没有稿费。我们的稿费真少,现在的跟50年代的差得不太多,物价涨了几十倍了,靠稿费吃饭你要饿死了!”
他不喜欢官场那一套。“国民党里好多重要人物都是我的同学、好朋友,要做官早做了,我不加入;跟共产党很多重要人物也是好朋友。我跟周恩来在重庆就认识,1945年国共合作谈妥之后政协成立,他开座谈会总有我;陈毅在上海当市长时,开座谈会总请我,我给他提经济方面的建议。他在很多场合说,'周有光的建议都很好,但我不在他也实现不了!’但我也没加入共产党。后来胡愈之说,没有一个组织关系不方便,我就参加了民盟,其实什么都不管。《群言》是民盟的刊物,我给他们写文章,20个编委现在就剩我一个。政协开会,我跟毛主席也碰到过,拍了几次照,但从来不挂。许多人把重要人物的照片挂在墙上,我只挂家里人。”
妻子张允和80岁时回忆昔日恋爱情景,写了篇《温柔的防浪石堤》,“两个人不说一句话。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是《罗密欧和朱丽叶》,小书签夹在第某幕、第某页中,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什么'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这个不怀好意的人,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他轻轻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虽然她没有用一吻“洗尽了罪恶”,但从此,“她的一生的命运,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
提到这篇文章,周有光笑了:“恋爱的文章嘛,大家都喜欢看。我老伴去世前一天晚上有朋友来拍照,第二天发病就去世了。她的心脏不大好,93岁,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他在纸上写下“93”这个数字,画个圈,让保姆找来一本张允和的自述文集《曲终人不散》,送给记者,署“周有光代张允和赠”。他始终叫她“我的老伴儿”,质朴情深。
人家看他是100多岁的长者,常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都是光明的,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沈从文的本事比我大
人物周刊:您跟张允和先生的恋爱故事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
周有光:人家对我们的恋爱很感兴趣,可是我的兴趣在学问上面,不在家庭生活上面,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我的老伴儿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做过两广总督、两江总督。到她父亲的时候,家里败落了,但还是很有钱。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跟蔡元培、蒋梦麟做朋友,离开本乡,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直到今天还在。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跟我妹妹同班。她到我家里玩,我们很早就认得。我跟她的关系,可以分为3个阶段。苏州阶段,好多人一块出去玩;上海阶段,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杭州风景好,是恋爱最好的地方,这是恋爱阶段了。后来结婚就到外国去了。
沈从文跟三妹(张兆和)的恋爱是另一种。他在中国公学教书,给三妹写情书,三妹找到校长胡适,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胡适说,他又没有结婚,向你表示好感没有错。这句话讲完三妹就很不高兴,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要不要我跟你父亲讲讲?三妹气得扔下信就走了。(大笑)沈从文本事比我大,你不理我信照样写,你看也好不看也好,一封一封来。他们后来到了山东大学慢慢好起来。我说沈从文脸皮老厚的!我一点不用追,我跟老伴儿是流水式的,他是冲击性的。
人物周刊:据说您给张允和先生写信说,“我很穷,怕不能给你幸福。”是真的吗?
周有光:对。他们家太有钱了!我们家也是大家,但太平天国把我们家打掉了。那时我很穷,我说我害怕不能给你幸福。她回了10页纸,说,幸福是要靠自己创造的。我们在杭州很有趣味,礼拜天去玩,不能手牵手,走路还要离开一段。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面,我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我们走得慢他也走得慢,故意听我们讲话。后来,我们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他坐在我们旁边,问我,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我说来了3年了。他说怪不得她中国话说得这么好!我的老伴儿鼻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他以为她是外国人!
人物周刊:您觉得金钱对婚姻重要吗?
周有光:可以说重要也可以说不重要。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的,可是在这个社会里面不能没有钱。有许多人为了钱结婚,也有人为了钱闹离婚,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我主张恋爱不仅要爱,还要有敬。许多人离婚是因为对对方没有敬重的心。我们两个人吃咖啡、喝茶,都是举杯齐眉,表示敬重。既有爱又有敬,婚姻会比较圆满。我跟我老伴儿,结婚70年,美满70年。我一个孙女在美国,买周年礼给我们,发现印好的卡片就到60年,没有70年的。人家问我们保姆,他们吵架吗?保姆说不吵架。其实也吵,但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不会哇啦哇啦让保姆听见。都是为别人的事,不是为两个人的事。我对什么事都是乐观态度,加上我既要爱又要敬的婚姻观,我们很幸福。
要以世界视角看中国
人物周刊:您曾将文字的历史分为三期:原始(形意)文字时期,古典(意音)时期和字母(表音)时期,汉字在宏观分期中处于古典时期。这3个历史时期是不是文字发展的必然轨迹?您曾说要让汉字字母化“等五百年吧”,但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字母化是不是一种历史趋势?
周有光:人类文字发展分几个阶段,不同学者看法不一样,我比较了几十种看法之后,把它分3个阶段,原始文字、古典文字和字母文字。原始文字是不成熟的,它不能全部记下我们想说的,尤其是虚指,有些部分要靠你自己记。汉字是古典文字,重要的古典文字还有两河流域的楔形字、古埃及的象形字和美洲的玛雅文。玛雅文一度失传了,差不多600年没有人认识,后来一个俄罗斯人把它认出来了。我在1956年搞到了俄罗斯的资料,第一个把它介绍过来。可是几年之前举行大规模的玛雅文化展览,只有玛雅文没有玛雅文解释,他们不知道玛雅文已经看得懂了!
古典文字作为符号是很难认的,之后有了字母文字,这是高度思维的结果,也是发展趋势。在咱们国家,有人争论我们的拼音能否成为文字。拼音化有两个含义:广义的拼音化,比如用拼音发短信、给汉字注音,方便了很多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他们觉得汉字很难。80年代到欧美去讲学,有个教授问我,你们汉字有没有1000个?他以为1000个就不得了了,我说我们通用汉字有7000个。他吓坏了!狭义的拼音化,就是把拼音变成正式的文字,这个很困难。拼音从理论上讲当然可以成为文字,但要真正成为文字,不仅要我能写,还要你能看懂,100年后的人能看懂。人家问我最短要多久,我说你等500年吧!
人物周刊:您曾举文艺复兴的例子旁证对“华夏文化”应该“温故而知新”,对古代文化的精华加以提高和发展,再创造新的文化。您对当前的“国学热”怎么看?
周有光:民国那时候就有好多人说不要用“国学”这两个字。什么叫“国学”?只是中国有“国学”吗?我就用“华夏文化”来代替“国学”。我主张研究华夏古代的东西,温故而知新。近来复古风很厉害,其中一种是真正的复古,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这是错误的。孔夫子说“述而不作”,先把古代的东西学好,不要乱七八糟自己搞,这个态度开头是很对的,但再进一步就不行了。我们今天要“述而又作”,社会是进化的,我们要学古代的,也要创造今天的。孔夫子是谨慎,说不要创造,其实他创造了很多东西。这就是正确的复古态度,不仅继承,还要发展和更新。
人物周刊:除了向内观照华夏文化之外,您一直很关注全球化的问题。
周有光:我是学经济出身,1955年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之后领导让我做文字改革,我就改行了。研究语言文字学时我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缺点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所以我写成了《汉字改革概论》,把群众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当时发行量很大,日本很快就翻译过去了。
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比如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这个问题很重要,我从50年代开始研究,一直到80多岁把它写成书,叫做《世界文字发展史》,补充了现代的知识,跟外国联系,把汉字的学问扩大到世界。
前两天我看到这本《许倬云访谈录》,有一段话很对,大意是说过去我们讲爱国,现在全球化年代不能这么讲了。法国人爱法国,德国人爱德国,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要爱人类,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这种想法在英美很早就有了,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一点,出版社说写得太心急了,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了。说真的,迟早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趋势。
文化不分国家。但我们这里,《人民日报》好多文章还是老一套,现在大学政治课都是老师讲给天花板听。要从世界看国家,不能从国家看世界,老一套的宣传迟早要改掉的。
我们很多社会科学处于玄学阶段
人物周刊:您曾提及历史发展的轨道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从听任自然到改造自然;在政治方面,从神权到君权到民权,从专制制度到民主制度;在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从迷信盲从到独立思考。您这个轨道的设想是怎么产生的?
周有光:社会的发展可以从好多角度看,主要是3个: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经济方面有3个高峰:农业化、工业化、信息化。中国农业化发展特别好,值得骄傲;工业化我们落后了,现在靠引进外包经济慢慢好起来,但这是初级阶段;信息化我们也进入了,比较快,特别是手机。但也在低阶段,最近不是正跟谷歌吵架吗,就是信息化的问题。
政治是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再到民权政治,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民主制度3000多年前古希腊就有了,可美国发展得比别的地方快。欧洲传统势力大,有很强大的特权阶级。我常说贪污很简单的,有特权有保密权,当然可以贪污,一民主特权没用处了,所以许多人要反对民主。
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再到科学思维。人家问我,你105岁,还能写文章,有什么长寿之道?我说没有,是上帝太忙了,把我忘了,这就是神学思维;玄学思维是推理性的,譬如我们看到太阳早上从东方升起晚上从西方落下,推出地球绕着太阳转;科学思维要靠实证,所以我们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人物周刊:您觉得当下中国处于什么阶段?
周有光:民主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在美国多了两样东西:第一是电视辩论。美国选举总统要在电视上面辩论。这两天新闻说,英国这个最早开创民主的国家一直没有电视辩论,也宣布今年首相大选要开始电视辩论了;第二是国际观察。他在国际上有3个重要的观察团,谁选举他就派人来看,看了也不讲话,回去之后才讲话,把你这个选举的真假看得很清楚。我们的选举,我这个老头子不能出去,什么人代替我选、选什么人,我都不知道。
我们改革开放已经改了很多了,全部都改是不可能的。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要求民主,这是自然趋势。当然民主不是有利无弊的,但利多一点。很多人问为什么欧洲帝国主义垮台了而美帝国主义没有。有人说美国条件好,有两个洋保护它,那南美洲为什么直到今天还很糟糕?关键是美国有民主。
欧洲国家垮在殖民地上,美国用技术创新代替殖民,用许多新方法赚你的钱,你还要感激它。最近《阿凡达》这么火,他们要给我买票,买不到。北京人家里几十样电器,90%都是美国的。最近我们跟美国吵,不行,吵不过它。全世界的网络有一个主根服务器,在美国;12个根服务器,9个在美国。它控制全世界的网络,怎么跟它打仗呢?美国花了3天时间切断萨达姆的通讯系统,不到一个礼拜美国坦克就开到了巴格达城里。所以不能用老办法对付它。怎么对付它?要研究!它最怕我们的科技进步!
我们的自然科学越来越发达,用的是科学思维,但我们的社会科学还很不发达,自己限制自己,有很多处于玄学思维阶段。有一次《群言》杂志开座谈会,清华大学的一个教授讲,他的一个朋友从美国回来,女儿跟着回来读中学。老师让她说读完《卖火柴的小女孩》有什么感想,她说资本主义不好,害得这个孩子很苦,社会主义要注意不要这样做。老师批她一个零分。他朋友就去找老师。老师说,你怎么这么教孩子,要告诉孩子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有坏事的!家长说,这不是叫她讲假话吗?老师回答,这不叫假话,叫思想引导!
这显然是玄学思想,不是科学思想。我们至少在社会科学方面还停留在玄学时代,很多思想没有引进来。比如没有引进教育学,教育搞得很糟糕。许多社会规律在我们这里都不起作用。
整个来讲我们还在第二阶段。我们是在前进,速度是比较快的,这一点是很好的。“满招损,谦受益”,假如这样,我们可以发展得更好一些。
- 上一篇:上一篇:小超人李泽楷的烂尾神话
- 下一篇:下一篇:王学圻:演戏就是一场轮盘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