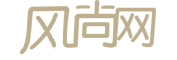钮承泽:生命是半场华丽的实验
时间:2010-08-11 00:56 来源:他生活

这个城市从来不会有人预告。没有晴天,没有承诺,没有温柔细语,一来就把你的脑袋蒙住,转身离开了就不知道能不能回头。有点狠,有点大,有点笨重,还有点拥挤。名声不是太好,但是每个由远及近观望的人,把希望和理智放进来过滤,都会剩下两个字:中心。
这里是北京。
飞机降落在首都机场,这是钮承泽第二次来到这里。但这里又是他的家。这跟他生活的台北不同,不比台北硬,但是却温柔有礼貌。相比之下,台北更犀利。
现在,他坐在面前,长长地舒了口气。因为他知道自己总是要回到这个地方的。但是这一次,他终于拍了一部自己认为不错的电影,也带着它回到家人身边。于是“昨天一晚上哭了三次”。大姑、三叔、堂兄弟姐妹、外甥女……面色黑瘦的钮承泽细数着他家族的人,指尖的烟灰顺势落下。
在钮承泽心里,台湾与大陆,既熟悉又陌生。“同文同种,一脉相传,但是因为历史因素曾经有过长久的隔断,可是现在却做密切交流。我有很多好朋友,包括我亲弟弟都在北京发展。虽然存在着物理上的距离,但是直航也就几个小时。距离已经不在了。”
他的确是个演艺资历很深的艺人。9岁接触表演工作,17岁就发下豪言,要做自编自导自演的全才电影人。他跟侯孝贤一起工作过,侯孝贤对他影响很大,但他当时就知道自己不会成为第二个侯孝贤。“我想拍的那种电影在《艋》里面还挺有脉络可寻:剧情丰富,情感真实,技术优良,然后让观众跟着哭跟着笑,走的时候还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带走点什么的。”
可以这么认为,他是先演电影,再看电影的。当时台湾有新电影运动,大陆出现了第五代导演。于是《黄土地》、《红高粱》、《大阅兵》等等他都有看过,但是真正有了一些特别的观影乐趣的,还是后面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秋菊打官司》、《有话好好说》等等。他啜了一口茶,背了句台词:“安红,我想你想得睡不着觉……”
说他是个贪心的导演,他摇摇头,“我一点都不贪心。我只是想拍有内容的大众电影,容易看、容易懂的。我本身就是一个通俗的人。也许是有点贪心。我讨厌用艺术和商业区分电影,只有好看的和不好看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在这其中我又想要有自己的艺术语言。可能在这个方面是贪心的。我又不想去复制什么,但是这些电影势必都会是我的养分。”
只是真正等到他开始可以做自己想要的电影时,他已经进入人生的下半场了。“年龄是一个残酷的问题。我发现自己眼睛已经开始花了,也会容易疲倦。现在有空更愿意躺在椅子上听音乐看书。我现在相信因果,我会接受。我等着看未来会怎么样。我在前年某一天,突然发现现在的我就是以前我想要的我。当初我在十几岁的时候,我就想现在的我。”
经历过这些,钮承泽忽然开始喜欢现在的自己。以前经常是讨厌、逃离自己。“我人生的下半场在进行一场华丽的实验。虽然我仍然有我卑劣的人性存在,我仍然有我的缺点,但是现在我已经不苛责我的卑劣了,我会跟我的欲望相处,不再被宰治,我不反对成功,但是成功必须符合我的人生观和品位。”
“这给我很大的信心,就算我中间有一个很不快乐很惨的过程,但是命运还是把我带到了这里。于是我对未来很有信心。我敢于想象20年后的我是个什么样子。”
Q:台湾电影大多都在表现自己的回忆和乡愁,你自己呢?
A:每一辈的创作者都有自己的情结,这不是机关算尽的,或者是技术能够展现的。他们一定会有自己的情怀。事实上,虽然成长背景不同,对世界的看法不同,时代不同,所以我也希望可以拍我的时代,我的内心,但是养分都来自生命的经验。
Q:你有满族血统,从小生长在将军府邸,外婆和妈妈也都在大学的语言中心教中文。这样的生长环境对你现在最大的影响是?
A:首先我必须说,我不是权贵子弟。虽然我外公是个军人,是将军,我们确实住在一个大宅里。但这不是一个权贵,也不是既得利益者,他是一个浪漫的人、在八年抗战中投笔从戎,因为命运作弄而到了台湾。我长大的过程中,常常听到外公外婆和父亲聊起自己的家乡。父亲常常讲起炒肝、豆汁,他们是很认真很认命的带着乡愁的人,不曾大富大贵。但因身为将军,有人脉和很多朋友。
Q:经常熬夜吧?
A:我是个夜猫子,向来晚睡晚起。我以前在台湾会有个毛主席俱乐部。因为看了毛泽东医生回忆录,里面对毛泽东的一些生活作息有记录,提到毛主席每天生活没有规律。看书、接见人、考虑问题,拖到困了就睡,然后起来就做任何想做的事情。这种生活方式有放松的快乐。可是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很强烈,可是我知道没有多少时间了。所以我开始调整自己,希望规律生活。虽然还没有开始执行。
Q:从你最开始踏入娱乐圈到现在,你自己最大的改变是什么?不变的是什么?
A:我觉得一切都是别人给我的,对自己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一方面说自己要做这个做那个,但是一方面却离自己的目标越来越远。自己年轻的时候工作也不是很努力,就是懵懂的。可是随着这一路走来,人生当然有很多阶段。当然看来一次比较大的困顿和挫折,常常觉得自己没有碰到想演的角色,在当导演上也常常得不到满足,但是看看就是这些困顿、折磨、挫折才是我创作的养分,它逼着我用现在的方式去跟世界沟通。不变的是我的敏感,我的脆弱,我的心里的那个小豆子,小承泽,我的羞怯。我的善良与任性。
Q:《艋》让你最有面子的地方?
A:太多地方了。其实真的现在的掌声已经是额外的奖励了。在制作它的过程中就已经充满感动了。我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因为很多人愿意相信我。跟这么一群兄弟工作,在限制之内我们从来没有放弃一点让作品变得更好的可能。这整个是一场华丽的恋爱,很多人,这个一点一点从无到有,这个过程中太多感动,就已经获得很多了。更何况还得到了这么大的回响,都的是额外的鼓励。
Q:你被义气捆绑过吗?
A:当然有。这个电影就可以看到我的警示意味。人在青春期荷尔蒙大量分泌,身体正在剧烈改变,脑袋还不成熟,我们开始跟同龄人合作,想要展现、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是人类社会化的开始,人是群体动物,需要建立一些东西。义气往往被当作最高指导,成为捆绑彼此的工具。当然义气是美的,否则我也没有不会有哥们,也不会觉得被支持,有安全感。但是我们需要有说不的勇气。
Q:现在最大的遗憾?
A:现在的我,会意气风发,但回到家里,还是很寂寞、没有老婆孩子和家庭。
- 上一篇:上一篇:马克思:在世博会看见历史的端倪
- 下一篇:下一篇:渡边淳一:说说情欲那点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