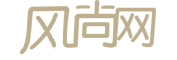冯德伦:怀才不遇的世界
时间:2010-08-11 00:30 来源:雅虎
他一定希望我叫他“导演”。这件事情他已经努力了有些日子,最后他如愿了。《跳出去》是他的电影,他没有演,他不会去演的,他要让他的导演身份和精力足够纯粹,他是“指挥”,“指挥”,需要“智慧”,是全才,而不能“只会演”一些什么。

冯德伦坚信世界上存在“怀才不遇”,并列出了公式:在北京,1000个做摇滚的人可能有5个会红;但500000个做演员的人当中,红的也只有5个;导演有多少冯德伦没统计过,但他对前5有兴趣。他的IQ有158,但他不懂得兼容,所以当演员风生水起,做导演就浑然忘却曾经辉煌,从新起点开始全力以赴。
冯德伦 人生不兼容
他一定希望我叫他“导演”。这件事情他已经努力了有些日子,最后他如愿了。《跳出去》是他的电影,他没有演,他不会去演的,他要让他的导演身份和精力足够纯粹,他是“指挥”,“指挥”,需要“智慧”,是全才,而不能“只会演”一些什么。
《Burn after reading》(《阅后即焚》)中有一群笨蛋,整部片子都在惶恐,其中一个笨蛋竟然问了一个聪明的问题“PC or Mac?”,他知道PC与Mac不会兼容。他有他认为难的事情,当你从冯德伦口中听到“我是冯德伦”时,就像《蝙蝠侠》中每600秒出现一次的那句“我是蝙蝠侠”一样糟糕,所以冯德伦兼容不了自己,不愿提自己的名字。这似乎有些刻意的回避,冯德伦很怕自己给人的感觉太过主观或者主动。“努力不用每分钟都讲出来”是他的不二法门,所以他开始不出演自己的电影,不出专辑,只是捧着便当、不刮胡须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导演后面小小的写上“Stephen Fung”,就像伍德斯托克的猫声鸟,难辨纲目。“兼容”有那么难么?他说有。冯德伦的IQ值或许有158那么多,跟李开复不相上下,但他却不懂得更多事情的“兼容”,他把自己的半生摘得干干净净:脾气塞在单色T恤下面,爱情塞在别人看不到的遮掩处,电影随便塞给什么人看,梦想夹在起司里,每天早上随面包一起独自享用……

星爷叫我去开会
2006年的一天,周星驰打电话给冯德伦,让他“下午来开开会”, 会议主旨是讨论一个故事,其实就是后来的《长江七号》,可惜冯德伦没搞清楚星爷在讲什么。最后星爷抛了一个问题出来,“如果一个村姑要跳hippop你有什么感觉”,没过多久《跳出去》开机了。
没有人相信两位导演同时插手一部片子会有通畅的过程,执导的想法就像云彩,周星驰可能希望它飘向左边,冯德伦可能希望右边,不过周星驰没有过多施压,他告诉冯德伦,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飘向右边好了。
这本应该叫《舞动人生》或者《芭蕾之梦》之类的译名,《Billy Elliot》九年前就已经搞得一大片法兰西人哭的稀里哗啦。片子离不开惯有的套路,一个叫Billy Elliot的小子坚持梦想的过程中遭遇伦理、人情最后终于踮起脚尖。冯德伦为这部片子介绍了很久,时间甚至可以与自己理应宣传的电影《跳出去》对峙十五分钟。影片和歌曲其实没有好看、难听一说,只要情节、歌词与自己的过往沾边儿就算拍正了马屁——很少有人去听没有血肉的轻音乐——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听《那一夜》或者罗百吉……
冯德伦与Billy Elliot几近相同的是十二岁左右都开始为一件事物所沉迷,Billy Elliot是薄底白鞋,冯德伦是吉他。大多数男人儿时都渴望蓄起长发,虽然长大后他们会在街上对留着披肩的男人暗竖中指。因为头发过长冯德伦没少被爸爸大骂,却始终顶了过来。当时,包括现在他都不想成为偶像,而只是像摇滚乐手那样提着琴箱四处串场,爽玩同时赚得微薄之盐。

走私摩托车
美国与加拿大交接处一边陲小镇,一天一名中年男子骑着摩托车过境,车后驮着一箱沙子。边境警察将他拦下,询问箱中所为何物,男子回答是沙子,警察检查完毕随即放行。就这样过了一年,中年男子每天都会驮着一箱沙子过境,终于有一天,警察恼怒了:“你实话告诉我我绝不抓你,你是不是在走私,到底在走私什么?”男子考虑了五秒钟,答道:“摩托车”。
这也是人们对待娱乐人物的心态,就很像愚蠢的警察,总觉得神秘,总是在盯着莫须有的一处并为之癫狂。我们对着MSN、QQ、微博一整天之后根本无暇专注于某人,充其量只是看看娱乐首页都有谁在“跳梁”。冯德伦在这一点或许吃了些小亏,他不愿每走一步就摆堂设宴诏告天下,这对他来说还不及与场地租用商讨价还价实在得多,他只希望每过一段时间自己都有些前进,比如观众的一句“这次你拍的《跳出去》确实比《精武家庭》好看了很多。”
冯德伦一类人很容易跳进自己为自己划出的麦田圈,这种喜欢将自己闷在家里但又不觉得“闷”的宅者很多时间都在拧巴顺其自然究竟要怎么个顺法,主角活着还是死掉更容易振聋发聩那些银幕几米开外品着香蕉奶棒的爱哭的人,当然这是私下的事情。 他说自己目前还没有“风格”可言,他的电影有可能被认出是冯德伦导的,但不排除朱德庸、刘德华、郭德纲,或者艾德?伍德……

天下大同
千真万确,每个人都曾对着好莱坞大喊:I have一个dream!电影之于好莱坞,就像相声掉进天津卫一样,每个人都知道“柳活”、“砸卦”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可能是深藏不露的剧作家。住在好莱坞的日子,不小心就入了戏。某一天,冯德伦随便找了一家Coffee bar坐下喝东西,跟服务生聊了几句,对方突然俯身过来透露:“其实我是一名演员”,说完转身继续工作,这多少让冯德伦有些好奇。不止如此,过了几分钟,收银员将一叠纸摔在吧台上,对着那位正在打咖啡的服务生大声喝斥:“剧本就不是这样写的!”他是编剧,客串了一下收银员……冯德伦突然发觉自己被印在了胶片上,以为是真实生活,却被摄像机收入镜头,这样的日子刺激有趣。
混好莱坞冯德伦收获不少,除了美国人说出“That’s all”时的嘴脸,他还利用充分的无聊时间学会了各种抬高身价的戏法——比如语录标示——比周董的“哎哟,不错哦”以及某个魔术师的“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早了不知多少年。
然而电影是不能唬人的,两件事情使冯德伦乖乖拍起好电影:拍《跳出去》期间,剧组去距离上海八小时车程的某农村取景,本来已经与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谈好了价钱,租用他家院子拍摄,不料拍摄过程中一个女人突然杀了出来挡住镜头阻止拍摄,理由想必是轨道、补光灯等大型设备妨碍了她的家禽散步之类的,实则就是渴望加些租地费用。一面工作人员与“包租婆”交涉,另一面冯德伦安排再架起几架机器到对面去,以将“包租婆”引开拍摄场地,不料“包租婆”完全认得清楚哪个机位正在拍摄,始终盯着主机位不放,最终只得花钱免灾。就像费劲心思将片中的张雨绮扮丑一样,冯德伦为基层人民的专业性伤透脑筋。

冯德伦坚信世界上存在“怀才不遇”,并列出了公式:在北京,1000个做摇滚的人可能有5个会红;但500000个做演员的人当中,红的也只有5个;导演有多少冯德伦没统计过,但他对前5有兴趣。他的IQ有158,但他不懂得兼容,所以当演员风生水起,做导演就浑然忘却曾经辉煌,从新起点开始全力以赴。
冯德伦 人生不兼容
他一定希望我叫他“导演”。这件事情他已经努力了有些日子,最后他如愿了。《跳出去》是他的电影,他没有演,他不会去演的,他要让他的导演身份和精力足够纯粹,他是“指挥”,“指挥”,需要“智慧”,是全才,而不能“只会演”一些什么。
《Burn after reading》(《阅后即焚》)中有一群笨蛋,整部片子都在惶恐,其中一个笨蛋竟然问了一个聪明的问题“PC or Mac?”,他知道PC与Mac不会兼容。他有他认为难的事情,当你从冯德伦口中听到“我是冯德伦”时,就像《蝙蝠侠》中每600秒出现一次的那句“我是蝙蝠侠”一样糟糕,所以冯德伦兼容不了自己,不愿提自己的名字。这似乎有些刻意的回避,冯德伦很怕自己给人的感觉太过主观或者主动。“努力不用每分钟都讲出来”是他的不二法门,所以他开始不出演自己的电影,不出专辑,只是捧着便当、不刮胡须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在导演后面小小的写上“Stephen Fung”,就像伍德斯托克的猫声鸟,难辨纲目。“兼容”有那么难么?他说有。冯德伦的IQ值或许有158那么多,跟李开复不相上下,但他却不懂得更多事情的“兼容”,他把自己的半生摘得干干净净:脾气塞在单色T恤下面,爱情塞在别人看不到的遮掩处,电影随便塞给什么人看,梦想夹在起司里,每天早上随面包一起独自享用……

星爷叫我去开会
2006年的一天,周星驰打电话给冯德伦,让他“下午来开开会”, 会议主旨是讨论一个故事,其实就是后来的《长江七号》,可惜冯德伦没搞清楚星爷在讲什么。最后星爷抛了一个问题出来,“如果一个村姑要跳hippop你有什么感觉”,没过多久《跳出去》开机了。
没有人相信两位导演同时插手一部片子会有通畅的过程,执导的想法就像云彩,周星驰可能希望它飘向左边,冯德伦可能希望右边,不过周星驰没有过多施压,他告诉冯德伦,如果你有足够的信心,飘向右边好了。
这本应该叫《舞动人生》或者《芭蕾之梦》之类的译名,《Billy Elliot》九年前就已经搞得一大片法兰西人哭的稀里哗啦。片子离不开惯有的套路,一个叫Billy Elliot的小子坚持梦想的过程中遭遇伦理、人情最后终于踮起脚尖。冯德伦为这部片子介绍了很久,时间甚至可以与自己理应宣传的电影《跳出去》对峙十五分钟。影片和歌曲其实没有好看、难听一说,只要情节、歌词与自己的过往沾边儿就算拍正了马屁——很少有人去听没有血肉的轻音乐——所以有那么多人喜欢听《那一夜》或者罗百吉……
冯德伦与Billy Elliot几近相同的是十二岁左右都开始为一件事物所沉迷,Billy Elliot是薄底白鞋,冯德伦是吉他。大多数男人儿时都渴望蓄起长发,虽然长大后他们会在街上对留着披肩的男人暗竖中指。因为头发过长冯德伦没少被爸爸大骂,却始终顶了过来。当时,包括现在他都不想成为偶像,而只是像摇滚乐手那样提着琴箱四处串场,爽玩同时赚得微薄之盐。

走私摩托车
美国与加拿大交接处一边陲小镇,一天一名中年男子骑着摩托车过境,车后驮着一箱沙子。边境警察将他拦下,询问箱中所为何物,男子回答是沙子,警察检查完毕随即放行。就这样过了一年,中年男子每天都会驮着一箱沙子过境,终于有一天,警察恼怒了:“你实话告诉我我绝不抓你,你是不是在走私,到底在走私什么?”男子考虑了五秒钟,答道:“摩托车”。
这也是人们对待娱乐人物的心态,就很像愚蠢的警察,总觉得神秘,总是在盯着莫须有的一处并为之癫狂。我们对着MSN、QQ、微博一整天之后根本无暇专注于某人,充其量只是看看娱乐首页都有谁在“跳梁”。冯德伦在这一点或许吃了些小亏,他不愿每走一步就摆堂设宴诏告天下,这对他来说还不及与场地租用商讨价还价实在得多,他只希望每过一段时间自己都有些前进,比如观众的一句“这次你拍的《跳出去》确实比《精武家庭》好看了很多。”
冯德伦一类人很容易跳进自己为自己划出的麦田圈,这种喜欢将自己闷在家里但又不觉得“闷”的宅者很多时间都在拧巴顺其自然究竟要怎么个顺法,主角活着还是死掉更容易振聋发聩那些银幕几米开外品着香蕉奶棒的爱哭的人,当然这是私下的事情。 他说自己目前还没有“风格”可言,他的电影有可能被认出是冯德伦导的,但不排除朱德庸、刘德华、郭德纲,或者艾德?伍德……

天下大同
千真万确,每个人都曾对着好莱坞大喊:I have一个dream!电影之于好莱坞,就像相声掉进天津卫一样,每个人都知道“柳活”、“砸卦”是什么东西,每个人都可能是深藏不露的剧作家。住在好莱坞的日子,不小心就入了戏。某一天,冯德伦随便找了一家Coffee bar坐下喝东西,跟服务生聊了几句,对方突然俯身过来透露:“其实我是一名演员”,说完转身继续工作,这多少让冯德伦有些好奇。不止如此,过了几分钟,收银员将一叠纸摔在吧台上,对着那位正在打咖啡的服务生大声喝斥:“剧本就不是这样写的!”他是编剧,客串了一下收银员……冯德伦突然发觉自己被印在了胶片上,以为是真实生活,却被摄像机收入镜头,这样的日子刺激有趣。
混好莱坞冯德伦收获不少,除了美国人说出“That’s all”时的嘴脸,他还利用充分的无聊时间学会了各种抬高身价的戏法——比如语录标示——比周董的“哎哟,不错哦”以及某个魔术师的“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早了不知多少年。
然而电影是不能唬人的,两件事情使冯德伦乖乖拍起好电影:拍《跳出去》期间,剧组去距离上海八小时车程的某农村取景,本来已经与一户人家的男主人谈好了价钱,租用他家院子拍摄,不料拍摄过程中一个女人突然杀了出来挡住镜头阻止拍摄,理由想必是轨道、补光灯等大型设备妨碍了她的家禽散步之类的,实则就是渴望加些租地费用。一面工作人员与“包租婆”交涉,另一面冯德伦安排再架起几架机器到对面去,以将“包租婆”引开拍摄场地,不料“包租婆”完全认得清楚哪个机位正在拍摄,始终盯着主机位不放,最终只得花钱免灾。就像费劲心思将片中的张雨绮扮丑一样,冯德伦为基层人民的专业性伤透脑筋。
- 上一篇:上一篇:席琳-迪翁:我心永恒
- 下一篇:下一篇:鸥洋:巴金说我画的就是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