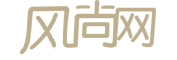昆曲京城生活新宠
8月4日,一个平常的工作日之夜。位于北京北四环的九朝会里,正在安静地酝酿着每周三晚惯例的昆曲演出。
开场前半小时,观众们陆续入场,落座。他们大都是中年人。在装潢得古色古香的戏楼里,灯光开了不到一半,略显昏暗。
台下低声交谈的声音、与戏台边乐师摆弄乐器时不时发出来的声响交杂在一起,让记者颇有些坠入梦境般的恍惚。
寻求心灵的宁静
无疑,在许多听昆曲的人心里,将昆曲本身比喻为一朵曾经盛开过的莲花似乎再合适不过。如今,这朵莲花的花瓣再次舒展,随之穿越时空而来的香气令人心醉 几年前,在电视台工作的赵先生迷上了昆曲,成了昆曲演出的“常客”。在与记者的谈话中,他不仅能够脱口而出众多昆曲曲牌,更是对昆曲的渊源与现状有一番见解。

昆曲
“京剧之所以能走入千家万户,就是在‘八个样板戏’的推动下。”他耐心地说,“但是昆曲,却还没有达到人人皆知的境地。”由于工作的原因,赵先生几乎时刻都在追踪新鲜的人和事。不过,他说,自己需要的并不是这些。“现在,昙花一现的东西太多了,都跟‘流星’似的。但昆曲,能让人在现代社会中沉静下来,寻求心灵的宁静”。
赵先生对昆曲的情有独钟很快“传染”给了妻子王女士。记者眼前的她,盘着头发,穿着旗袍,如陈逸飞油画笔下的传统女子般细腻优雅。“我的工作时而繁忙、时而清闲。听着昆曲,我会放松下来,更好地调整自己的节奏。”
这次来看九朝会的昆曲演出,赵先生还带来了一位台湾同胞。记者从他这里也听到了来自海峡对岸的讯息。
在台湾,昆曲也很流行,不过,受众一般同时满足两个要素———有经济实力、年龄较大。“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昆曲,还蛮期待的。”他笑着告诉记者。 第一次看戏是否会在昆曲绵长的唱词中昏沉睡去?心中暗暗升起疑问的记者在开场之后,瞄了一眼这位台湾同胞。结果发现,他像个小学生,把胳膊叠放在前排座椅的椅背上,前倾着身体,睁圆了眼睛,认真极了。
戏台上,两位昆曲演员分别饰演《思凡》和《下山》中的小尼姑色空。二人华丽的扮相配以精湛的表演,再加上圆润悠长的唱腔,一颦一笑、一字一句、一步一趋,皆为意境。难怪台下的观众,个个目不转睛。
此情此景,正应了鼓师李先生在开演前的话,“台下观众都得老老实实坐着,怎么可能有如雷贯耳的一声‘好’啊”。
当晚的演出人员均来自北方昆曲剧院。面对越来越壮大的昆曲受众群,他们显得很淡然。
专程赶到九朝会来接受记者采访的北方昆曲剧院副院长曹颖说:“20多年前,有一次我们五六十人的演出,台下只有3名观众,但我们依然尽力去演。演出结束后,这3名观众到后台来,感动地和演员一一握手。如今,昆曲演出的上座率不断上升,有时还能满座。”欣赏昆曲之美的理由 昆曲“暗潮汹涌”的这几年来,作为文化中心的北京,自然不会错过这场好戏。很多人也是在这股“暗潮”中领略到了昆曲之美,从而慢慢喜欢上了这个“国宝”
在当晚的演出人员中,有一位年轻的笛师———丁文轩,他从音乐学校考入北京昆剧团。小丁的装扮似乎格外“抢眼”———白衬衫、黑背心、牛仔裤,这个面目清秀的年轻人很“哈韩”。
丁文轩告诉记者,在他的朋友圈里,不乏比他年长的“忘年之交”。赵珑渊就是其中的一位。
“我是湖南人,从小就听花鼓戏。”他对记者说,“念高中的时候,我接触了元曲,于是对昆曲有了文字上的了解”。
2003年单位组织活动,初次听到昆曲的他一下子爱上了“百戏之祖”———昆曲。“昆曲给人一种很空灵、雅致、婉转的感觉。”他说。 赵珑渊说,这几年,自己周围不少人都在赶昆曲的“潮流”。这种古时文人士大夫们的享受,如今成了现代人生活的“奢侈品”。“有点小资情调的意思吧。”他笑了笑。
不过,赵珑渊并不是来看热闹的“门外汉”。他最为中意的是《游园惊梦》。因为工作繁忙,他不能经常观赏“现场版”,因此,他在家中备了影碟,“没事的时候就看看”。夜深人静时,电视荧幕前的他,至动情处,总会潸然泪下。
在北京工作的山东人刘先生自认为还没踏进昆曲的门槛。不过,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一个欣赏者的快乐。
一年前,他在朋友的邀请下去北大听了《厅会》和《百花赠箭》两场折子戏。“感觉特别好,我拍了好多照片。”刘先生话语里透着愉快,“昆曲可以说是一个美的结合体,一点都不单一,这可不是浮躁社会中的‘快餐’。”
抱着“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的心态,“外行人”刘先生开始向周围的朋友推荐他心中的中国文化的“根儿”。“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人问我,昆曲是不是昆明的地方戏啊。”他笑着说。不过,渐渐地,越来越多的朋友成了和他一样的昆曲迷。
现在,刘先生时不时地去剧场欣赏昆曲。他说,几个小时的昆曲听下来,不仅不枯燥,反而动人得很。看戏之余,与昆曲演员聊天时,刘先生发现的演出“破绽”偶尔能得到“你怎么看出来的”的回应。“这是我最得意的时刻。”他说。
欣赏昆曲的人越来越多,这在从事专业演出的丁文轩看来却很淡然。“现在不是都说昆曲是‘新贵族运动’嘛。”他嘴角带着笑意。来自“正规军”之外的追捧 除了各地昆曲剧院这支“正规军”之外,“业余民兵队”也存在于民间的昆曲爱好者中间。北京昆曲研习社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北京昆曲研习社是北京昆曲爱好者研究和传习昆曲艺术的业余文化团体,由俞平伯教授等业余昆曲爱好者发起。虽然早在1956年,北京昆曲研习社就成立了,但被人逐渐熟知并关注,还是最近几年。
“我们每个月都至少有一次活动。就是大家聚在一起,共同交流和学习。”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一名老成员告诉《法治周末》记者。
目前,北京昆曲研习社的主要成员包括昆曲的资深爱好者,以及一些专业从事昆曲的艺术家。
“主要是做一些昆曲的交流和研究,大家活动时都会围在一起唱。”这位成员说,“我们现在还会去北大等高校组织一下‘曲会’,其实也就是带着大家一起来唱昆曲,让大家对昆曲有更深的了解。”
当问及是否有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喜欢上昆曲时,这位成员说:“可能是这几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的原因吧,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接触昆曲,其中一些人会对昆曲产生喜爱。但能够成为真正的昆曲爱好者,并使其成为自己生活爱好中的一部分,还是需要时间来说话。”
毋庸置疑,昆曲所代表的美学趣味是南方的,但这并不会让其静止于一时一地。有人认为,“正是由于它是文人雅趣的典范,才具有极强的覆盖能力,有得到广泛传播的可能,并且在传播过程中,基本保持着它在美学上内在的一致性”。
也许,正因为这样的“美”,在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盛极一时的昆曲才能在诞生600年后,重现其流光溢彩。
“可能还真是因为白先勇的推动,这几年,看昆曲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杂了。”北方昆曲剧院鼓师李先生说。
李先生对记者说:“有时候,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完,我一看台下,居然有很多青年学生。这些孩子们也坐在台下,认认真真地听。” 近几年来,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昆曲的受众群越来越广。曹副院长向记者透露,在刚刚过去的180多天里,北方昆曲剧院已经演出了220场。“有时一天能演5场。”他说,“这是前几年无法想象的。”
提到北方昆曲剧院这支“正规军”之外的“业余编制”,曹副院长说:“除了北京昆曲研习社,其实还有一些昆曲爱好者们自发组成的昆曲团体。我们需要这些民间的业余组织和团体,协助我们一起推广昆曲、普及昆曲,让更多的人关注、接受并喜欢上这个‘国宝’。”
追者各有心
1000个读者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昆曲亦不例外。在如今这股被戏称为“新贵族运动”的昆曲潮流面前,人们态度各异。有人充满信心,相信昆曲会因此而得以薪火相传;有人依然徘徊,不知究竟是附庸风雅还是寄托心灵;有人满腹愤懑,认为这股风潮有使昆曲沦为产业之嫌……
“这样的效果也许要得益于白先勇当年的青春版《牡丹亭》产生的新闻效应。”高丙中教授说,“这是一个过程。起初,人们对昆曲不甚了解,对其价值缺乏认识。自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确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后,人们开始逐渐注意起昆曲来,并希望可以对这个‘国宝’有所了解。”
很多昆曲爱好者都觉得,昆曲能够带给他们“心灵的宁静”。“其实也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刘先生告诉记者,“昆曲对听众的影响应该是潜移默化的,对我而言,听昆曲让我对它能够有越来越深的了解,进而越来越喜欢它。”
一位热爱昆曲的北京大学学生却表达了另外的看法。“我总觉得,现在的昆曲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炒作,一种附庸风雅。”她对记者说,“当时白先勇的青春版《牡丹亭》来北大百年讲堂演出,对外宣传的,是服装有多精致、多复古。演出搞得掌声雷动。但问题是,昆曲不是一件掌声雷动的事情啊……”
这位学生告诉记者,昆曲近几年的重新流行,很大程度上在于各方努力,“可如果让一群搞文化产业的人去‘折腾’昆曲,那昆曲必然会成为一个‘产业’而存在”。
“但这样,总比慢慢地彻底没有人去关注要好。问题是,如今关注昆曲的,究竟有多少人是真心想让昆曲传承和发展下去的呢?”她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等待上场的鼓师李先生似乎回应了这种很有代表性的忧虑。
“昆曲啊,你就不要管它,就让它在这儿呆着,让它自己发展,足够了。”说完,他起身疾步走进戏楼,帘布那边,演出正在等着他。
- 上一篇:上一篇:收藏红木家具如何着手 "老红木"精品细细玩味
- 下一篇:下一篇:地下写作的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