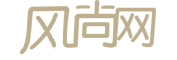格非:用稀缺的精英立场写小说
时间:2010-08-11 00:52 来源:时代周报
 作家格非
在精神质地上,格非就像是一位古代的隐士,思绪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思考着一个个玄虚的命题。在这些奇异的文本中,时间发生着微妙的扭曲,父亲可能是杀害自己亲生骨肉的凶手,一种名为“青黄”的植物与妓女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在先锋文学的河流中,格非的写作总是显示出某种形而上的特质,一位习惯于冥想的天行者,总是感觉到与现实的格格不入。
从丹徒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格非找到他理想的居所了吗?现在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他似乎比上世纪80年代更安静了,阅读古籍,或者远远地躲在意大利山间的修道院里写他的小说,时间缓慢流淌,染白了头发,写作对于他来说似乎更像是一种修行。
顶着毒太阳,在清华大学正门口见到等候在那儿的格非教授。和十年前比,他的容貌和神情没有大的变化,甚至发型也一样,只是皮肤更黑了一些,最大的差别是:头发白了太多。卸去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行政职务,格非显得轻松而沉着。
他现在主要的心思都放在最新的长篇小说之上。《山河入梦》的续集,《人面桃花》三部曲的大结局,很期待。进入新世纪(002280,股吧),格非的步调明显放慢,除了一些短篇和随笔,《人面桃花》三部曲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写作时间。
格非,这个有着浓重学院派气质的小说家每时每刻都在经历被时代的潮流抛在一边的心痛历程。这或许就是他多年之前写作《敌人》—中国先锋派的第一部长篇—一个隐秘的理由,对于读者来说,敌人这个词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对自我的破坏。
追忆丽娃河畔
时代周报: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小说家和诗人,16岁你考上华东师大中文系,是“文革”后的第一届考生吧?喜欢中文系才考的吗?
格非:应该是17岁。我1964年出生,1981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当时我喜欢中文和历史。就我个人而言,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最喜欢中文和历史—相对来说,可能中文更好一点吧,它和我的气质性格更接近。我所有的志愿一律填的都是中文、历史,没有填过其他。
时代周报:“文革”后期,你们学校没有停课吗?
格非:“文革”时候比较乱,小学初中都是很不正规的,都是村里的农民来教。高中以后呢,也是半正规,我现在英文不太好可能就跟当时我的老师发音不太好有关系,口语方面我的发音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对那些最初教我英语的老师印象很深,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发音就很成问题。
时代周报:大学期间看得比较多的作品是什么?
格非:什么都看。我记得我们进华东师大,有一个阅读书目,大概列了100本书,主要是西方作品,我记得这个书目中没有一部是中国的作品。这个书目是中文系里的老师开的,每个学生的要求都一样,每个学生必看。
时代周报:照理说当时应该还比较保守吧,怎么都是西方书目?
格非:从当时的老师们来讲呢,他觉得你的本行就是做中国语言文学的,这是你的专业,你所有的知识都需要他们在四年的大学中教给你,但是外国文学方面我们的老师都特别重视。这也不奇怪,他们会期望每个学生都去阅读经典作品。残酷的童年回忆
时代周报:像你、苏童、北村这一批的作家,在小说中常常会显露出一种弑父弑子的情结,你觉得这种残酷性是怎么形成的?
格非:在《敌人》中,父亲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情节设置恐怕和我对文化的思考有一些关系。或者是那个年代,我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有关。
在《敌人》中,实际上外部的敌人他并没有真正出现,我只是通过一系列的迹象来暗示他的存在。比如他们家的孩子一个一个死去,却不知道是谁杀的,我只是把人的恐惧找到一个形式表达出来而已。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征服内心的敌人才能真正地克服恐惧。所以我在小说中也设计了一个内在的线索:这个父亲无力承担他的家族真正存在的敌手,找不到这个敌手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他把孩子杀掉来平息、安抚某种命定的东西,把这样一个悲剧交给命运去承担。这跟我小时候对于民间文化的接触和我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的看法有关。
时代周报:跟童年时候“文革”的记忆也有关系么?
格非:恩,你刚才的问题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暴力有施暴就有受虐,无论是施暴还是受虐的一方,暴力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司空见惯的。当然也是日常生活日常经验的一个部分,生活无时无刻不存在暴力,当然也无时无刻不在恐惧,那是日常化了的,不像在今天至少有各种各样的法律保障(或者说假设的保障),但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屏障,暴力和你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想这种恐惧感和我的童年记忆有密切关联。
时代周报:你的作品看出来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包括看法和视角。
格非:即使在今天来看,那个立场我仍然觉得还是必要的。
中国有精英么?我觉得很奇怪,很多人说中国应该平民化,应该取消这个精英的立场,可是你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中国很多精英都是伪精英,都是为了争夺话语权力、占领道德的或知识的制高点的“精英”。那个年代真正的精英发育还不够成熟,所以导致我们国家在90年代之后大的变化之后几乎看不到什么精英。所以这个精英的立场从今天来看也是重要的。
拒绝回到好莱坞
时代周报:2000年以后你从上海移居北京,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到了北京以后是否觉得北京是一个你想象中的文化氛围很好的城市?
格非:这个差别是事后追认的,是我事后我可以概括的。当时我挺喜欢上海的,我并不愿意来北京,但是没有办法,由于家庭的变故,我不得不到北京来,而不是我喜欢不喜欢北京的问题。到清华等于是在北京找了一个落脚点,联系了很多高校,最后选择在清华。
时代周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读古籍的呢?是对西方价值观开始有反思?然后也是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过程?
格非:我从内心上感到有两个要求,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开始出国了,到西方的各个国家去,真正地观看他们的社会,这个过程中我的想法会有很大的变化。我想知道西方究竟是怎么样的?我想知道它们真正的文化、环境,对问题的解释。二是我内心的变化,一个人到了三十多岁,内心有这种要求:不仅要解释社会,还要解释个人。我过去认为文学可以帮助社会进步,可以揭露某种真相,可以揭示某种真理。可是到了80年代,我发现文学可能更重要的是关注我们自身对生命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我觉得只懂一个肯定不对,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打算花一点力气来研究中国的古籍。有的人修养很好,从小这些都具备,我不一样,我是被时代逼着,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要求来解决自己的困惑。说这些我无非是要说明,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完全是一种内心的要求。
时代周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电影的?为什么对伯格曼、费里尼这样的导演感兴趣?
格非:我当年在上海开过一门“伯格曼和先锋电影”的课。那时候录像带还不普及,我都是从美国、中国台湾、香港托人找片子。我给他们放电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学生不太接受,很多课上得也都是莫名其妙。但是如果让我去讲好莱坞电影我也没什么兴趣,我把电影视作与小说同样重要的表达社会的一种手段。我特意选了一些与社会变化、历史、哲学相关的电影给学生放,然后进行讨论,但是不成功。他们不希望认真地做研究,不希望对于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世界采取去了解的态度。他们甚至给学校写信,要求我重新回到好莱坞来。
最近我在清华给大家开了这门课,开了一个学期,课名叫“电影文本与社会”,我还是比较满意,很愉快。我给他们介绍伯格曼、费里尼、安哲洛普罗斯这样导演的作品,我不知道清华的学生是怎么想的,因为他们对伯格曼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单周放映双周讨论,结果通过我们讨论、他们交的作业,我发觉我的学生都很喜欢这门课,有很多学生表示他们还会继续来听这门课。我想可能今天的学生跟过去比更有包容性。
时代周报:不知道你现在还担任不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工作?
格非:管教学的副系主任我做了六七年之后就不做了,很累,我做系主任也有一年多,尤其做了系主任之后,压力大到想要把自己消灭掉一样。于是2007年我断然辞职,因为它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和写作。
时代周报:你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你对现在的作协体制怎么看?
格非:我虽然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但已经多少年没有什么来往了。他们的作协代表大会也不会让我这样的人去参加。作协的活动我也很少参与。我本来以为作协有一个权力保障委员会可能对我们打官司有点帮助,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很多地方对作家的服务也很差。我可能跟一些作协的领导铁凝、陈建功私人关系比较好,其他我就不知道作协对我还有什么用了。比如国外有作家代表团来,他们可能会请我去陪着吃个饭什么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联络。
作家格非
在精神质地上,格非就像是一位古代的隐士,思绪游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思考着一个个玄虚的命题。在这些奇异的文本中,时间发生着微妙的扭曲,父亲可能是杀害自己亲生骨肉的凶手,一种名为“青黄”的植物与妓女之间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瓜葛。在先锋文学的河流中,格非的写作总是显示出某种形而上的特质,一位习惯于冥想的天行者,总是感觉到与现实的格格不入。
从丹徒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格非找到他理想的居所了吗?现在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的他似乎比上世纪80年代更安静了,阅读古籍,或者远远地躲在意大利山间的修道院里写他的小说,时间缓慢流淌,染白了头发,写作对于他来说似乎更像是一种修行。
顶着毒太阳,在清华大学正门口见到等候在那儿的格非教授。和十年前比,他的容貌和神情没有大的变化,甚至发型也一样,只是皮肤更黑了一些,最大的差别是:头发白了太多。卸去了清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行政职务,格非显得轻松而沉着。
他现在主要的心思都放在最新的长篇小说之上。《山河入梦》的续集,《人面桃花》三部曲的大结局,很期待。进入新世纪(002280,股吧),格非的步调明显放慢,除了一些短篇和随笔,《人面桃花》三部曲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写作时间。
格非,这个有着浓重学院派气质的小说家每时每刻都在经历被时代的潮流抛在一边的心痛历程。这或许就是他多年之前写作《敌人》—中国先锋派的第一部长篇—一个隐秘的理由,对于读者来说,敌人这个词已经成为一种象征:对自我的破坏。
追忆丽娃河畔
时代周报: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涌现了一批优秀的小说家和诗人,16岁你考上华东师大中文系,是“文革”后的第一届考生吧?喜欢中文系才考的吗?
格非:应该是17岁。我1964年出生,1981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当时我喜欢中文和历史。就我个人而言,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最喜欢中文和历史—相对来说,可能中文更好一点吧,它和我的气质性格更接近。我所有的志愿一律填的都是中文、历史,没有填过其他。
时代周报:“文革”后期,你们学校没有停课吗?
格非:“文革”时候比较乱,小学初中都是很不正规的,都是村里的农民来教。高中以后呢,也是半正规,我现在英文不太好可能就跟当时我的老师发音不太好有关系,口语方面我的发音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对那些最初教我英语的老师印象很深,刚开始学英文的时候发音就很成问题。
时代周报:大学期间看得比较多的作品是什么?
格非:什么都看。我记得我们进华东师大,有一个阅读书目,大概列了100本书,主要是西方作品,我记得这个书目中没有一部是中国的作品。这个书目是中文系里的老师开的,每个学生的要求都一样,每个学生必看。
时代周报:照理说当时应该还比较保守吧,怎么都是西方书目?
格非:从当时的老师们来讲呢,他觉得你的本行就是做中国语言文学的,这是你的专业,你所有的知识都需要他们在四年的大学中教给你,但是外国文学方面我们的老师都特别重视。这也不奇怪,他们会期望每个学生都去阅读经典作品。残酷的童年回忆
时代周报:像你、苏童、北村这一批的作家,在小说中常常会显露出一种弑父弑子的情结,你觉得这种残酷性是怎么形成的?
格非:在《敌人》中,父亲杀死了自己的孩子,这样的情节设置恐怕和我对文化的思考有一些关系。或者是那个年代,我对传统文化的看法有关。
在《敌人》中,实际上外部的敌人他并没有真正出现,我只是通过一系列的迹象来暗示他的存在。比如他们家的孩子一个一个死去,却不知道是谁杀的,我只是把人的恐惧找到一个形式表达出来而已。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征服内心的敌人才能真正地克服恐惧。所以我在小说中也设计了一个内在的线索:这个父亲无力承担他的家族真正存在的敌手,找不到这个敌手而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所以他把孩子杀掉来平息、安抚某种命定的东西,把这样一个悲剧交给命运去承担。这跟我小时候对于民间文化的接触和我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失落的看法有关。
时代周报:跟童年时候“文革”的记忆也有关系么?
格非:恩,你刚才的问题是很好的一个问题。暴力有施暴就有受虐,无论是施暴还是受虐的一方,暴力在我们那个年代是司空见惯的。当然也是日常生活日常经验的一个部分,生活无时无刻不存在暴力,当然也无时无刻不在恐惧,那是日常化了的,不像在今天至少有各种各样的法律保障(或者说假设的保障),但在那个时候呢,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屏障,暴力和你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我想这种恐惧感和我的童年记忆有密切关联。
时代周报:你的作品看出来是一个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包括看法和视角。
格非:即使在今天来看,那个立场我仍然觉得还是必要的。
中国有精英么?我觉得很奇怪,很多人说中国应该平民化,应该取消这个精英的立场,可是你要知道,上世纪80年代中国很多精英都是伪精英,都是为了争夺话语权力、占领道德的或知识的制高点的“精英”。那个年代真正的精英发育还不够成熟,所以导致我们国家在90年代之后大的变化之后几乎看不到什么精英。所以这个精英的立场从今天来看也是重要的。
拒绝回到好莱坞
时代周报:2000年以后你从上海移居北京,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到了北京以后是否觉得北京是一个你想象中的文化氛围很好的城市?
格非:这个差别是事后追认的,是我事后我可以概括的。当时我挺喜欢上海的,我并不愿意来北京,但是没有办法,由于家庭的变故,我不得不到北京来,而不是我喜欢不喜欢北京的问题。到清华等于是在北京找了一个落脚点,联系了很多高校,最后选择在清华。
时代周报: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读古籍的呢?是对西方价值观开始有反思?然后也是重新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过程?
格非:我从内心上感到有两个要求,一个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我开始出国了,到西方的各个国家去,真正地观看他们的社会,这个过程中我的想法会有很大的变化。我想知道西方究竟是怎么样的?我想知道它们真正的文化、环境,对问题的解释。二是我内心的变化,一个人到了三十多岁,内心有这种要求:不仅要解释社会,还要解释个人。我过去认为文学可以帮助社会进步,可以揭露某种真相,可以揭示某种真理。可是到了80年代,我发现文学可能更重要的是关注我们自身对生命的理解,在这个问题上,东西方对此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我觉得只懂一个肯定不对,这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打算花一点力气来研究中国的古籍。有的人修养很好,从小这些都具备,我不一样,我是被时代逼着,内心充满了强烈的要求来解决自己的困惑。说这些我无非是要说明,我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完全是一种内心的要求。
时代周报:你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电影的?为什么对伯格曼、费里尼这样的导演感兴趣?
格非:我当年在上海开过一门“伯格曼和先锋电影”的课。那时候录像带还不普及,我都是从美国、中国台湾、香港托人找片子。我给他们放电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学生不太接受,很多课上得也都是莫名其妙。但是如果让我去讲好莱坞电影我也没什么兴趣,我把电影视作与小说同样重要的表达社会的一种手段。我特意选了一些与社会变化、历史、哲学相关的电影给学生放,然后进行讨论,但是不成功。他们不希望认真地做研究,不希望对于一个自己不了解的世界采取去了解的态度。他们甚至给学校写信,要求我重新回到好莱坞来。
最近我在清华给大家开了这门课,开了一个学期,课名叫“电影文本与社会”,我还是比较满意,很愉快。我给他们介绍伯格曼、费里尼、安哲洛普罗斯这样导演的作品,我不知道清华的学生是怎么想的,因为他们对伯格曼们其实很陌生。我们单周放映双周讨论,结果通过我们讨论、他们交的作业,我发觉我的学生都很喜欢这门课,有很多学生表示他们还会继续来听这门课。我想可能今天的学生跟过去比更有包容性。
时代周报:不知道你现在还担任不担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副主任的工作?
格非:管教学的副系主任我做了六七年之后就不做了,很累,我做系主任也有一年多,尤其做了系主任之后,压力大到想要把自己消灭掉一样。于是2007年我断然辞职,因为它严重影响到我的生活和写作。
时代周报:你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你对现在的作协体制怎么看?
格非:我虽然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但已经多少年没有什么来往了。他们的作协代表大会也不会让我这样的人去参加。作协的活动我也很少参与。我本来以为作协有一个权力保障委员会可能对我们打官司有点帮助,其实也没有什么帮助,很多地方对作家的服务也很差。我可能跟一些作协的领导铁凝、陈建功私人关系比较好,其他我就不知道作协对我还有什么用了。比如国外有作家代表团来,他们可能会请我去陪着吃个饭什么的,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联络。
- 上一篇:上一篇:“战斗一生”华君武
- 下一篇:下一篇:专访孟非:尊重少数人,宽容个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