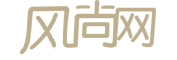陈寅恪诞辰120周年 传承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
时间:2010-08-10 23:54 来源:未知
 晚年陈寅恪
今年是陈寅恪(1890—1969)诞辰120周年,海内外出现了各种纪念活动。由陈寅恪的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合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4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同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卞僧慧编纂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书均用繁体字排版。7月,蔡鸿生著《读史求识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上特别注明“纪念陈寅恪先生诞生120周年”。
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曾经对陈家姐妹说:“作为女儿,你们已经尽心尽力办了很多事,第一个是整理出版父亲的作品集,第二个是在庐山为父亲选择了一块清净的墓地,第三个事情就是要撰写回忆录了。”陈流求、陈美延姐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也同欢乐也同愁》的合著方式是:“陈流求、陈美延近两年同住一处,方便合作书写。陈小彭则通过电话、电脑联系。”她们在书的后记称:“这本小册子从文学角度看,应没有什么价值;但从史料角度看,似有点弥补与佐证作用。”
生活细节与家庭故事是《也同欢乐也同愁》的一大特色。蔡鸿生认为:“最珍贵的就是其中所流露出的亲切感,很多事情只有他们亲人自己才知道的。”陈寅恪三个女儿取名,皆有来历。流求出生时,台湾已被日本占领,而“流求”是台湾的古称;“小彭”则隐喻澎湖列岛,“长女名‘流求’,次女名‘小彭’,不仅听起来十分关切,更有深一层的意思:要我们姐妹切勿忘记在当时被日本侵占,而原来属于我国的台湾、澎湖。”“美延”则由陈寅恪的父亲散原老人取名,出自《荀子·致士》:“得众动天,美意延年。”
《也同欢乐也同愁》通过孩子的眼睛观察陈寅恪的交往史。如陈寅恪与吴宓这对生死之交:“一天家里做好了晚餐,掌灯已久还不见父亲回家,便出去寻找,才发现他在离家不远的小道上,跟吴宓伯父聊得格外投机,忘记了时间,后来这种事情还常有发生。”抗战时期陈寅恪一家在香港生活,女儿们回忆:“赵元任伯母(杨步伟)及赵家姐姐们赴美前,途经香港时来访。记得那天,我们家采购的菜肴比平日丰富很多,赵伯母性格爽朗,亲自动手切肉丝,刀功娴熟,流求在旁观看,很感意外,赵伯母发现孩子诧异的眼神,笑着说:‘别忘了我是大夫啊!’”“母亲和小彭曾陪赵伯父母购物,小彭注意到赵伯父在一家象牙工艺品商店,与售货员以标准粤语交谈,但速度没有本地人说得快,觉得奇怪。后来小彭才知道赵伯父是语言学家,用拼音将粤语拼出。”对赵元任夫妇的描述,极为传神,可与杨步伟的《杂记赵家》互为参照。
1948年12月,战火逼近北平,陈寅恪一家南下的情况是极为关键的史料。14日,陈寅恪到胡适家时,但见“胡伯母招待我们吃晚饭并住下,胡伯父则忙得不可开交,不是电话便是有人来找或是安排事情。”“这天夜里,父亲与郑天挺、邓广铭两位伯父彻夜长谈,几乎没有睡觉。”15日上午,胡适夫妇与陈寅恪一家同往机场南下。三个女儿回忆陈寅恪的事,到了1949年就收笔了。陈家姐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1949年后陈家旧事,是否续写,现正在研究、考虑之中。”
在《母亲》一章中,则补充了1949年以后父母生活的回忆,“也同欢乐也同愁”的诗句便是1955年陈寅恪为结婚纪念日而作的。而“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之句,也有真实写照。在女儿眼里,陈寅恪“每次遭受沉重打击后,常有一度情绪低落,但不久又会振作起来,积极投入教学、研究。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垂暮耄耋之年,以目盲骨折卧床之躯,写完八十多万字《柳如是别传》之后,仍不辍创作,直到红卫兵勒令助手离去,不准再制造‘毒草’才被迫停止工作。”从某种角度看,《也同欢乐也同愁》与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形成了一些史料互补。
现年99岁的卞僧慧是陈寅恪在1949年以前的学生。他集多年之功编纂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陈寅恪详尽的年谱,补了许多先前史料未及之处。陈家姐妹认为:“卞僧慧先生《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受蒋天枢先生重托,增补《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5年来卞老在艰苦条件下,亲自收集大量资料,加以取舍整理,在99岁高龄时得以面世,是一部严谨踏实的作品,应予充分肯定。”卞僧慧则在后记中写道:“世人每称先生为一代宗师,诚当之无愧。正当中国之大变局、世界之大变局,政历四代,游学东西洋十余年,博文卓识,终生献身学术。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直可谓千种矛盾、万种情思,胥可于先生一身见之。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先生人虽没,但其思想、学说之影响却从未停止。”
现年77岁的蔡鸿生是陈寅恪在1949年之后的学生。蔡鸿生在1955年至1956年,以“元白诗证史”选修生的身份,在金明馆听陈寅恪讲史论诗,后来著有《仰望陈寅恪》一书。在刚出版的《读史求识录》中,蔡鸿生通过学习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来研究历史:“陈寅恪先生关于‘在史中求史识’的教导,犹如‘在水中学游泳’一样,是平凡的真理,并没有什么玄机。”中山大学历史系从2008年10月开始摆放陈寅恪的铜像,蔡鸿生对着铜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算不上陈寅恪的‘入室弟子’,对他的感情既不敢谈‘继承’,也无从说‘走近’,只能说是‘仰望’。”而陈寅恪的学术精神核心,蔡鸿生认为可以通俗地称为“二要一不要”:要独立自由,要脱俗求真,不要曲学阿世。
1950年夏,陈寅恪全家于广州。余英时是陈寅恪后世相知者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渐成“显学”。
1958年秋天,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油印稿本,引起了精神上极大的震荡。当时余英时在美国的身份是“无国籍之人”,顿感有一种切身的体会,便写了一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多年后,陈寅恪的女儿陈小彭托人写信转告余英时:陈寅恪当年读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余英时清楚地记得,读到陈寅恪这四字评语后,“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上世纪80年代初,余英时写了《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两篇长文,引起了极大反响,后集成《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不过,余英时认为自己研究陈寅恪只是“人生中的偶然”。
真正促成“陈寅恪热”的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为了撰写此书,查阅了第一手的档案,并访问了邓广铭、王永兴等陈门弟子。他自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在超过千卷档案卷宗的翻阅积累上而成的,它交织着现实与个人精神的困惑与痛苦,以及久抑之下必蓄冲缺牢笼的气势。这或者是90年代中后期大陆人文思潮重又涌起新浪潮的一个缩影。”在书中,陆键东认为:“1963年陈寅恪曾作《感赋一律》,内有句云‘后世相知或有缘’。客观地说,余英时或许可算陈寅恪‘后世相知’者。”余英时则说:“陆键东的书有一个好处,我从前说的许多,人家驳我的,现在我就不用驳了。”
2008年,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出版。广东行政学院教授张求会认为:“此书成功的首要原因,是忠诚地实践了以诗史互证、古今交融、显隐并重、内外兼顾为主要表征的‘旧方法’。所谓‘旧方法’,既可以远溯到‘乾嘉之法’,也可以追踪到余英时先生首倡的‘以陈释陈’。”
张求会的《陈寅恪的家族史》是研究义宁陈氏的重要著作,他今年在报章上发表多篇文章,继续探讨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通过各种证据推断:“陈寅恪夫妇在‘时局日紧’之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通过马鉴、陈君葆谋划赴港,一面通过朱家骅、傅斯年准备赴台。”张求会以新发现的史料印证余英时在《跋新发现的陈寅恪晚年的两封信》中的论断:“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绝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使陈寅恪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公案有了进一步的解读。
陈寅恪是老海归
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定居广州,身后常被视为岭南学术文化的象征性人物,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后人所景仰。如今,陈寅恪故居被中山大学修缮一新,作为参观纪念之所。蔡鸿生就是在这里聆听陈寅恪讲课的,当时陈寅恪双目失明,但讲课非常认真。蔡鸿生回忆:“他讲课很容易接受,完全是口语化。虽然他的书用文言文写,可讲起课却跟我们平常谈话一样。”蔡鸿生认为那一代的本科生知识储备很差,虽然听课之前都有预习,但是相关知识面很窄,所以陈寅恪总尽可能讲得浅白一点,但是所提的很多事情仍是本科生所不知道的,所以陈寅恪要仔细地论证。然而,不久后时局所致的“误人子弟”罪名,大伤陈寅恪之心,从此不再讲课了。
陈寅恪的著作相继出版后,不仅在中国大陆学界引起重视,而且在华人学术界流传。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弱水是唐史专家,他认为:“陈寅恪的研究涵盖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对中古提出很多整体性的见解,针对现象提出解释性说法,确立了典范。陈先生提出了很多课题和典范性说法,使中国中古史研究立刻达到了别的领域一开始没有的深度和高度。他选择中古研究可能跟他所处的时代有关,那是中国重新跟西方发生密切交接的时代,这跟中古比较像。研究中古得出的教训对进入国际社会之中的中国有帮助,这个因素大概是边缘的,但让他的研究有特别的深度。另一方面,当他在研究中遇到某些问题跟现实对应的时候,他会表而发之。譬如《元白诗笺证稿》提到的有些东西,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社会风气和政治腐败使他有所感触,可是我觉得他的核心还是一个专业的学者。就与时代的关系而言,比较可讲的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他是一个敏感的人。”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回忆,当年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跟余英时第一次半聊天半面试时说:“看陈寅恪的东西,觉得他的表达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观点。这引文里的信息ABCD非常多,最后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读者在读这一段资料的时候,不知道他的逻辑推论是怎样进行的。”余英时当然知道这种看法很肤浅,但还是热心地推荐黄进兴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来余英时撰写《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书中一些文章时,黄进兴是第一读者。如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少学者的研究,仍然受到陈寅恪的影响。
蔡鸿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课时跟一些研究生说:“如果要学陈寅恪,学他的文章风格,首先你就通不过出版社,通不过杂志社,因为他著书的时候,是一段一段地引用资料和加按语的,别人不可能那么做。学陈寅恪,重要的是领会精神。”
蔡鸿生认为陈寅恪学术精神对当代的影响是:“我们要脚踏实地做学问。无论是钱锺书还是陈寅恪,他们的学问不能够悬空而学。钱锺书强调中西贯通,学理要‘打通’。而陈寅恪强调‘发覆’,有好多东西被历史所掩盖,需要我们重新弄清真相。要‘发覆’,要‘打通’,人家可是用了一辈子的功夫啊!前辈强调外来文化跟本土文化的关系,借鉴西方的同时,绝不能忘记传统。真正能够作贡献的是吸收西方的东西,然后在中国研究,以期有所创新。陈寅恪、钱锺书是老海归、大海归。钱锺书吸收很多西方的美学理论和文艺思路,在《谈艺录》中用来分析中国的古典诗话。陈寅恪到过法国、美国,但是自己做学问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现在中国跟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老前辈的做法对我们而言,不只是借鉴,同时也是榜样。”
晚年陈寅恪
今年是陈寅恪(1890—1969)诞辰120周年,海内外出现了各种纪念活动。由陈寅恪的三个女儿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合著的《也同欢乐也同愁》4月由三联书店出版;同月,中华书局出版了卞僧慧编纂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书均用繁体字排版。7月,蔡鸿生著《读史求识录》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上特别注明“纪念陈寅恪先生诞生120周年”。
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蔡鸿生曾经对陈家姐妹说:“作为女儿,你们已经尽心尽力办了很多事,第一个是整理出版父亲的作品集,第二个是在庐山为父亲选择了一块清净的墓地,第三个事情就是要撰写回忆录了。”陈流求、陈美延姐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也同欢乐也同愁》的合著方式是:“陈流求、陈美延近两年同住一处,方便合作书写。陈小彭则通过电话、电脑联系。”她们在书的后记称:“这本小册子从文学角度看,应没有什么价值;但从史料角度看,似有点弥补与佐证作用。”
生活细节与家庭故事是《也同欢乐也同愁》的一大特色。蔡鸿生认为:“最珍贵的就是其中所流露出的亲切感,很多事情只有他们亲人自己才知道的。”陈寅恪三个女儿取名,皆有来历。流求出生时,台湾已被日本占领,而“流求”是台湾的古称;“小彭”则隐喻澎湖列岛,“长女名‘流求’,次女名‘小彭’,不仅听起来十分关切,更有深一层的意思:要我们姐妹切勿忘记在当时被日本侵占,而原来属于我国的台湾、澎湖。”“美延”则由陈寅恪的父亲散原老人取名,出自《荀子·致士》:“得众动天,美意延年。”
《也同欢乐也同愁》通过孩子的眼睛观察陈寅恪的交往史。如陈寅恪与吴宓这对生死之交:“一天家里做好了晚餐,掌灯已久还不见父亲回家,便出去寻找,才发现他在离家不远的小道上,跟吴宓伯父聊得格外投机,忘记了时间,后来这种事情还常有发生。”抗战时期陈寅恪一家在香港生活,女儿们回忆:“赵元任伯母(杨步伟)及赵家姐姐们赴美前,途经香港时来访。记得那天,我们家采购的菜肴比平日丰富很多,赵伯母性格爽朗,亲自动手切肉丝,刀功娴熟,流求在旁观看,很感意外,赵伯母发现孩子诧异的眼神,笑着说:‘别忘了我是大夫啊!’”“母亲和小彭曾陪赵伯父母购物,小彭注意到赵伯父在一家象牙工艺品商店,与售货员以标准粤语交谈,但速度没有本地人说得快,觉得奇怪。后来小彭才知道赵伯父是语言学家,用拼音将粤语拼出。”对赵元任夫妇的描述,极为传神,可与杨步伟的《杂记赵家》互为参照。
1948年12月,战火逼近北平,陈寅恪一家南下的情况是极为关键的史料。14日,陈寅恪到胡适家时,但见“胡伯母招待我们吃晚饭并住下,胡伯父则忙得不可开交,不是电话便是有人来找或是安排事情。”“这天夜里,父亲与郑天挺、邓广铭两位伯父彻夜长谈,几乎没有睡觉。”15日上午,胡适夫妇与陈寅恪一家同往机场南下。三个女儿回忆陈寅恪的事,到了1949年就收笔了。陈家姐妹告诉时代周报记者:“1949年后陈家旧事,是否续写,现正在研究、考虑之中。”
在《母亲》一章中,则补充了1949年以后父母生活的回忆,“也同欢乐也同愁”的诗句便是1955年陈寅恪为结婚纪念日而作的。而“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之句,也有真实写照。在女儿眼里,陈寅恪“每次遭受沉重打击后,常有一度情绪低落,但不久又会振作起来,积极投入教学、研究。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垂暮耄耋之年,以目盲骨折卧床之躯,写完八十多万字《柳如是别传》之后,仍不辍创作,直到红卫兵勒令助手离去,不准再制造‘毒草’才被迫停止工作。”从某种角度看,《也同欢乐也同愁》与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形成了一些史料互补。
现年99岁的卞僧慧是陈寅恪在1949年以前的学生。他集多年之功编纂的《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陈寅恪详尽的年谱,补了许多先前史料未及之处。陈家姐妹认为:“卞僧慧先生《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是受蒋天枢先生重托,增补《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25年来卞老在艰苦条件下,亲自收集大量资料,加以取舍整理,在99岁高龄时得以面世,是一部严谨踏实的作品,应予充分肯定。”卞僧慧则在后记中写道:“世人每称先生为一代宗师,诚当之无愧。正当中国之大变局、世界之大变局,政历四代,游学东西洋十余年,博文卓识,终生献身学术。性极敏感,思富联想,而又痌瘝在抱,常怀千岁之忧。诚旷世之大师,不世出之人杰。直可谓千种矛盾、万种情思,胥可于先生一身见之。先生如精琢多面体之金刚石,一有光源即灿烂夺目。从先生可以见世界万象,从世界万象亦可以见先生。先生人虽没,但其思想、学说之影响却从未停止。”
现年77岁的蔡鸿生是陈寅恪在1949年之后的学生。蔡鸿生在1955年至1956年,以“元白诗证史”选修生的身份,在金明馆听陈寅恪讲史论诗,后来著有《仰望陈寅恪》一书。在刚出版的《读史求识录》中,蔡鸿生通过学习陈寅恪的治学方法来研究历史:“陈寅恪先生关于‘在史中求史识’的教导,犹如‘在水中学游泳’一样,是平凡的真理,并没有什么玄机。”中山大学历史系从2008年10月开始摆放陈寅恪的铜像,蔡鸿生对着铜像告诉时代周报记者:“我算不上陈寅恪的‘入室弟子’,对他的感情既不敢谈‘继承’,也无从说‘走近’,只能说是‘仰望’。”而陈寅恪的学术精神核心,蔡鸿生认为可以通俗地称为“二要一不要”:要独立自由,要脱俗求真,不要曲学阿世。
1950年夏,陈寅恪全家于广州。余英时是陈寅恪后世相知者
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研究,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渐成“显学”。
1958年秋天,余英时在哈佛大学偶然读到陈寅恪的《论再生缘》油印稿本,引起了精神上极大的震荡。当时余英时在美国的身份是“无国籍之人”,顿感有一种切身的体会,便写了一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多年后,陈寅恪的女儿陈小彭托人写信转告余英时:陈寅恪当年读过《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一文后,曾说:“作者知我。”余英时清楚地记得,读到陈寅恪这四字评语后,“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上世纪80年代初,余英时写了《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两篇长文,引起了极大反响,后集成《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不过,余英时认为自己研究陈寅恪只是“人生中的偶然”。
真正促成“陈寅恪热”的是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陆键东为了撰写此书,查阅了第一手的档案,并访问了邓广铭、王永兴等陈门弟子。他自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是在超过千卷档案卷宗的翻阅积累上而成的,它交织着现实与个人精神的困惑与痛苦,以及久抑之下必蓄冲缺牢笼的气势。这或者是90年代中后期大陆人文思潮重又涌起新浪潮的一个缩影。”在书中,陆键东认为:“1963年陈寅恪曾作《感赋一律》,内有句云‘后世相知或有缘’。客观地说,余英时或许可算陈寅恪‘后世相知’者。”余英时则说:“陆键东的书有一个好处,我从前说的许多,人家驳我的,现在我就不用驳了。”
2008年,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出版。广东行政学院教授张求会认为:“此书成功的首要原因,是忠诚地实践了以诗史互证、古今交融、显隐并重、内外兼顾为主要表征的‘旧方法’。所谓‘旧方法’,既可以远溯到‘乾嘉之法’,也可以追踪到余英时先生首倡的‘以陈释陈’。”
张求会的《陈寅恪的家族史》是研究义宁陈氏的重要著作,他今年在报章上发表多篇文章,继续探讨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通过各种证据推断:“陈寅恪夫妇在‘时局日紧’之际,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办法—一面通过马鉴、陈君葆谋划赴港,一面通过朱家骅、傅斯年准备赴台。”张求会以新发现的史料印证余英时在《跋新发现的陈寅恪晚年的两封信》中的论断:“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绝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使陈寅恪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公案有了进一步的解读。
陈寅恪是老海归
陈寅恪最后二十年定居广州,身后常被视为岭南学术文化的象征性人物,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后人所景仰。如今,陈寅恪故居被中山大学修缮一新,作为参观纪念之所。蔡鸿生就是在这里聆听陈寅恪讲课的,当时陈寅恪双目失明,但讲课非常认真。蔡鸿生回忆:“他讲课很容易接受,完全是口语化。虽然他的书用文言文写,可讲起课却跟我们平常谈话一样。”蔡鸿生认为那一代的本科生知识储备很差,虽然听课之前都有预习,但是相关知识面很窄,所以陈寅恪总尽可能讲得浅白一点,但是所提的很多事情仍是本科生所不知道的,所以陈寅恪要仔细地论证。然而,不久后时局所致的“误人子弟”罪名,大伤陈寅恪之心,从此不再讲课了。
陈寅恪的著作相继出版后,不仅在中国大陆学界引起重视,而且在华人学术界流传。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弱水是唐史专家,他认为:“陈寅恪的研究涵盖了魏晋南北朝隋唐,对中古提出很多整体性的见解,针对现象提出解释性说法,确立了典范。陈先生提出了很多课题和典范性说法,使中国中古史研究立刻达到了别的领域一开始没有的深度和高度。他选择中古研究可能跟他所处的时代有关,那是中国重新跟西方发生密切交接的时代,这跟中古比较像。研究中古得出的教训对进入国际社会之中的中国有帮助,这个因素大概是边缘的,但让他的研究有特别的深度。另一方面,当他在研究中遇到某些问题跟现实对应的时候,他会表而发之。譬如《元白诗笺证稿》提到的有些东西,是抗战时期大后方的社会风气和政治腐败使他有所感触,可是我觉得他的核心还是一个专业的学者。就与时代的关系而言,比较可讲的是《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他是一个敏感的人。”
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黄进兴回忆,当年他在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跟余英时第一次半聊天半面试时说:“看陈寅恪的东西,觉得他的表达方式很奇怪,常是先有引文,才有自己的观点。这引文里的信息ABCD非常多,最后拿的可能只是其中的B,读者在读这一段资料的时候,不知道他的逻辑推论是怎样进行的。”余英时当然知道这种看法很肤浅,但还是热心地推荐黄进兴到哈佛大学读博士。后来余英时撰写《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书中一些文章时,黄进兴是第一读者。如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少学者的研究,仍然受到陈寅恪的影响。
蔡鸿生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讲课时跟一些研究生说:“如果要学陈寅恪,学他的文章风格,首先你就通不过出版社,通不过杂志社,因为他著书的时候,是一段一段地引用资料和加按语的,别人不可能那么做。学陈寅恪,重要的是领会精神。”
蔡鸿生认为陈寅恪学术精神对当代的影响是:“我们要脚踏实地做学问。无论是钱锺书还是陈寅恪,他们的学问不能够悬空而学。钱锺书强调中西贯通,学理要‘打通’。而陈寅恪强调‘发覆’,有好多东西被历史所掩盖,需要我们重新弄清真相。要‘发覆’,要‘打通’,人家可是用了一辈子的功夫啊!前辈强调外来文化跟本土文化的关系,借鉴西方的同时,绝不能忘记传统。真正能够作贡献的是吸收西方的东西,然后在中国研究,以期有所创新。陈寅恪、钱锺书是老海归、大海归。钱锺书吸收很多西方的美学理论和文艺思路,在《谈艺录》中用来分析中国的古典诗话。陈寅恪到过法国、美国,但是自己做学问也是研究中国文化。现在中国跟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老前辈的做法对我们而言,不只是借鉴,同时也是榜样。”
- 上一篇:上一篇:邬君梅:三演宋美龄
- 下一篇:下一篇:阿Sa:用信仰憧憬纯真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