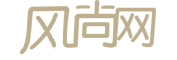造型师张叔平

《花样年华》中,我们忽略了张曼玉不再年轻的脸庞,却醉倒在她妖娆身体衬托出繁花似锦的旗袍上;《春光乍泄》里,我们从张国荣那件黄条开襟毛衣开始,深深触摸到那个男人寂寞的心。
平凡的生活,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服饰与色彩,让我们可以在多年以后记忆犹新。一切,要感谢那个叫名叫张叔平的男人,带给我们平庸之外的想像。
盛名之下的他始终坚守自己的方式生活——不爱抛头露面,衣着简单到只穿相同的款式,但不能舍弃两样东西:烟和酒。还有,每一部戏之前,都一样的没有安全感。
热爱电影的人几乎没有人忽略过“张叔平”这个名字,当然更多时候他是和另外两个名字——杜可风、王家卫连在一起被人们传奇般地重复着。这位被视作香港电影界首屈一指的美术鼻祖获奖无数,从香港电影金像奖到台湾电影金马奖到戛纳最佳艺术成就奖,但他极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于是在外人眼中更抹上一层神秘色彩。
见到张叔平是7月6日下午,上海虹桥迎宾馆一楼的咖啡厅,那会儿他正附身仔细地看着桌上的一叠底片,没和任何人说话。我坐在他正对面的沙发上观察眼前这个中年男人,眉目清秀,面色白皙,尤其是那双握着底片的手,细腻、修长,近乎苍白——这很吻合想像中一双出色的美术师的手。
我说“来采访您之前我的心情有些忐忑,因为您似乎一直不爱跟记者打交道”,他很温和地看着我笑,神情中带点无奈的懈怠感。他的国语还算流利,语速很慢,常常一个话题说到一半会跳开去,或者因受到现场某个人或声音的干扰而停顿,这时他就会笑着问:“刚才我们说到哪儿了?”然后抽出手边的“沙龙”点上,幽幽地吸上一口。
“您的名字总让人跟‘华丽’、‘优雅’之类的词产生联想”,张叔平很吃惊:“为什么?我以为人家听到这个名字会以为是个老头。”我告诉他没想到他这么年轻,他很文雅地说“谢谢”,然后感叹:“老了,50岁了。”“听说您是上海人?”他摇手:“那是他们乱说,我爸爸是无锡人,妈妈是苏州人。”
忽然发觉眼前的张叔平真的很坦白,完全没有戒心,而话题一旦打开,气氛便变得无比轻松。
初发电影梦——“我从14岁开始喜欢电影,到现在这个想法都没有改变。”
想像中14岁的张叔平应该是一个瘦削白净的少年,寡言而充满幻想。那是1967年的香港,一切氛围都不像现在这般新潮、明朗。那一年,张叔平看到了平生第一部让自己沉思的电影,并坚定地认为这一生会与电影结缘。
“当时看了一部电影叫《毕业生》,看完后心里很忧郁,不舒服,就像失恋了一样。等了一个礼拜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于是又去看了一遍,然后觉得完了。它跟我们平常看的电影不一样,以前我们小孩子都是看詹姆士.邦德那样的电影,很随便、很好玩,而《毕业生》讲故事的方法跟平常不一样。那时有很多严肃的影评和分析,我也就此喜欢上电影,看美国的、欧洲的各类影片,每个礼拜要看四五部。”
17岁那年,张叔平离家出走。回忆那段经历,他脸上有释然的笑意。“我爸爸很厉害,那时如果晚上超过12点不回家,他就会把门铃关掉,怎么按都不响;他不喜欢我的朋友到家里来;而老师不很认真打分的品行报告也常令我挨打……”再后来,父母离异,正处于反叛年龄的张叔平决定离开。先住在朋友家,慢慢找到了工作,在服装厂做过设计,也给一些影片做过副导演——张叔平开始接近梦想。
步入影视圈——“电影其实没有理论可讲!我做的时候觉得自己一定可以。”
给导演唐书旋做副导演的时候,张叔平决定去国外读电影,虽然他觉得并没有这个需要,因为“你做一部电影就知道整个过程了”,但那种环境吸引了他。不过传统的父亲很不乐意,好在当年答应过前妻,儿子想念书的话一定要让他念,但父亲告诫张叔平千万别对亲戚说是学电影,“爸爸认为那算什么玩意儿!他觉得很丢脸”。
至今张叔平都固执地认为理论知识全然没有用。“在加拿大念了三年电影,念完了也觉得没用。什么理论,每个理论都可以打破!你不觉得其实没有理论?一部电影你从头讲也可以,从中间讲也可以,全是碎片也行,只要好看。”
三年后的香港早就物是人非,很多人都不认识张叔平,接下来的一年他都没有找到工作。第二年去了一家美国品牌的服装公司,年轻的他整日做着40岁女人的衣服,“很闷的”。然后,有了转机——导演谭家明找到他。
张叔平真正意义上的美术设计就此起步,他还记得那部片子的主角是林青霞。“我觉得非常有把握,没有怕的东西。那次我做得特别过分,墙壁是蓝的,女人穿的是红的,林青霞又很漂亮,像广告一样,真是头脑简单(轻笑)!因为谭家明很喜欢戈达尔,而戈达尔非常喜欢红蓝白的色调。”于是,那样的浓烈让人们记住了张叔平,这跟他当初步入电影圈抱定的想法一致——第一次做表现多一点,人家就会留意你。
不想谈风格——“我有风格吗?如果没有写我的名字,你看不看得出是我做的?”
从《旺角卡门》开始,王家卫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张叔平的帮衬,到《花样年华》这里可谓达到极致,所有人都为张曼玉缭乱而妖娆的旗袍倾倒,但张叔平对于夸赞淡淡地笑:“那些衣服美吗?我原本的意图是想俗气一点的。我不觉得漂亮,花花绿绿的,不是有品位的,因为苏丽珍只是个秘书;至于《春光乍泄》,那里面的衣服其实很烂的,都是旧旧的;《东邪西毒》是古时候的故事,侠士不可能每天梳头烫衣服,所以穿得也很破……我觉得看一部电影的美术要从总体看,灯光、摄影、构图,不能分开。”
我请他评价一下自己的风格,他马上反问我:“有吗?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知道是我做的才说我的风格怎样怎样,如果没有名字,你看不看得出来是我做的?我的每一部戏都不会重复,用过的颜色、质感都会尽量避免。每部戏我都希望能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都把它当作第一部去做。”
那么灵感呢?“我先要知道做一部什么电影,然后会跑来跑去看一些东西,可能从一双鞋、一只皮包、一只碗、一棵树或一面墙壁就此引申开去,慢慢地放大了。”一直这样做下去,张叔平说希望不会有灵感枯竭的那天。
投缘王家卫——“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特别想做世界上没人做过的事,现在还是这么想。”
眼前的张叔平说话时常常给人“可有可无”的随意性,很少坚持,可从前他决不是这样的。那时年轻的他在创作上的坚持得让人不能相信。“我平常对吃什么穿什么去哪儿无所谓,但做事比较坚持,我要那个东西无论怎样都要出现,所以会想尽办法弄到,比如为了一种布的颜色,我会在家染好多遍。那时的想法是导演要什么,我一定给他更多,不允许别人批评我一句,不能有一点差错。我设计好的东西不能改一丝一毫,如果你不喜欢就算了,也不要给我钱!个性强得不得了。”要求完美的他很少跟导演讨论,更讨厌“规范”,这点和王家卫特别有默契,因此合作最顺。
“我和王家卫合作他的第一部电影时我们已是相交7年的朋友了,几乎天天在一起聊电影。我们一直有个目标,就是想做没做过的事。所以有一天他说要拍戏,我们一拍即合,彼此信任,沟通很好。”然后,张叔平也在不知不觉间感染了王家卫式的“随意”,“拍《阿飞正传》很幸运,想要的服装、道具都找得很顺利,到《重庆森林》时我开始换一种方式,下午拍戏我上午才去随意买些衣服,回来一试也不错。后来我觉得,创作是很奇怪的东西,哪有两个月前就设计好了的?其实王家卫不像外界说的没有剧本,当天要拍的戏当天会有剧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