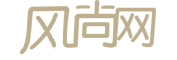伊斯坦布尔的城市之主
连续数日的上午,伊斯坦布尔都笼罩在阴天里,似乎有意让我们进入帕慕克所描绘的那种人人心事重重的景观。我们所住的苏丹艾哈迈德区是三大历史建筑——蓝色清真寺、艾亚-索菲亚清真寺以及托普卡珀宫——的所在地,三者自南向北连成一线,排列在海峡和地中海的交界处。从旅馆出门步行下坡十分钟,就能到达蓝色清真寺,原名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往北一些是艾亚-索菲亚清真寺,再往北就是早期苏丹们居住的托普卡珀皇宫。这片区域绿树成行、古迹林立,从西南往东北方向形成很规则的矩形,一片片小块草坪铺点其间,草坪的边缘立着通体白色的路灯灯杆,灯泡被笼在带有皇冠形尖顶和精巧边饰的玻璃罩里,很像国际象棋棋子里“皇后”的模样。
草坪之间,显眼地立着三根形态各有千秋的古柱:君士坦丁石柱、青铜蛇柱和狄奥多西方尖碑,沿着通往蓝色清真寺的主路排成一行。三大柱各有故事,我入境随俗,不由自主地喜欢上那根看起来最有残相的孔雀蓝色的蛇柱:它从地下伸出,所立基的地平面乃是当初君士坦丁大帝给都城选址的原始地面。
奥斯曼的帝王们把自己的宫殿建立在拜占庭的旧址之上,让“征服”一词得到最好的诠释。近百年来,考古人员从未停止在苏丹艾哈迈德区的发掘工作,试图分离垂直叠加的历史遗迹并让其各归其位,他们的成果包括一座由查士丁尼建造的“教皇地下水宫”,还有一大批拜占庭石板镶嵌画,被陆续收藏进了镶嵌画博物馆,最大限度复原后贴上馆内的四壁。
还不得不提及这城里的另一大景观。土耳其街道上多流浪狗,据帕慕克说,不是因为民众都欢迎它们,而是管不过来,只好任其散漫游荡。我们待的日子不长,但一路见到和抚摸过极多的狗与猫:它们在人们的腿脚之间穿行,在汽车和电车的头尾急匆匆跑来跑去;很多狗像一台台待机的电脑那样,躺在石子路面或缝隙很大的黑石路面上打盹,猫则尤爱居民区、清真寺、墓园这些地方,三五成群,寻找食物。它们,连同清真寺和广场上无处不在的鸽子一起,都和人一样共享地中海餐饮习惯——以面包为日常主食。

在我们看来如此乖顺的小畜,在《纯真博物馆》男主角凯末尔的眼里,却是“空无一人的黑暗小巷”的唯一住户,这些小巷两侧是水泥公寓大楼,“白天因为丑陋和破旧而让我难过”。不过,小说叙事的背景毕竟是20世纪70年代。今天这些旧楼即使没被拆除,据我们所见,也多被漆上了各式各样的涂鸦作品,更不用说在贝伊奥卢、贝西克塔什、西什利、埃米诺努这些商业味更重的地方。整整9年,凯末尔天天从富人区尼相塔什前往楚库尔主麻大街,去拜访他的情人芙颂及其父母和名义上的丈夫所居住的“黑暗小巷”的深处,这陋巷也由此一洗颓容,“充满了诗意和神秘”。
芙颂考驾照的一节,尤其拉近了帕慕克和我的距离:他不再炫耀自己的地方性知识,而真正关心起“众生”,关心起像考交规、路考、走考官后门这类鸡零狗碎的事情来。芙颂考问凯末尔“交通”的概念,对方答不上来,芙颂笑道:“交通是行人、动物、机动车在公路上的状态和行动。”
我猜测这是交规第一条里的话。原来在土耳其,“动物”是排在“机动车”之前的交通主体,土耳其的驾车人要像尊重行人通行权一样地关照过街的动物,不管它有没有主人。在伊斯坦布尔,我真的没觉得动物是点缀,是在两条腿丛林之间凑趣解闷的四条腿;我觉得所有生命的相互距离都很近,每一种生物——人、猫、狗、鸽子、燕子、鹳、黄嘴鸥、信天翁以及栗子树、橘树、柏树、托普卡珀宫外的木兰树——都是城市之主。
如果说穆罕默德二世是第一个主人的话,那么现在,城市属于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生命。他们背后是铅灰色的清真寺和宫殿,还有常常设在地势隆起的半坡上的墓园,向这凡间的生命通报神明的秘密。
- 上一篇:上一篇:香巴拉宫 拉萨第一个藏式精品酒店
- 下一篇:下一篇:唐蕃古道上的三江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