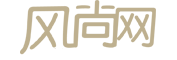
每次与白川抽烟,总会被打断。天台上(他)的熟人、展览后的拜访与合照、女儿的一百道脑筋急转弯解题。而当我们正儿八经把烟点上,试图找一些话题兼容进这几分钟的快活时光,天南地北都是家里长短。如何去讨论影像及其背后种种意向所指,怎么去讨论一个人,他的表达方式、创作过程——这些貌似都不是土象星座们擅长、点燃一根烟在路边、树下可以侃侃而谈的...
“荣光、爱与死亡通常会在同一种缺席中:它们从那种日常的在场中撤回。它们将存在置于自身之外,而存在就是这样走向自身的。”
白川个展 《虎的迷途》现场 |厦门三影堂
每次与白川抽烟,总会被打断。天台上(他)的熟人、展览后的拜访与合照、女儿的一百道脑筋急转弯解题。而当我们正儿八经把烟点上,试图找一些话题兼容进这几分钟的快活时光,天南地北都是家里长短。如何去讨论影像及其背后种种意向所指,怎么去讨论一个人,他的表达方式、创作过程——这些貌似都不是土象星座们擅长、点燃一根烟在路边、树下可以侃侃而谈的。
最终我们去厦门参加了由摄影集的系列作品选取而成的展览:
《虎的迷途》
策展人如此写到:“展览的主体即是由这一系列照片组成的记忆长廊,没有具体的时间和人物线索,就像我们突然陷入回忆时那般,过往的时刻随机地涌现。”
事实上在没有一个文字的摄影集中,可供摸索的时间线和反复出现的人物线索,标志性的事件,一切有序并清晰地展现着故事背后的可能。
而不确定的是人物主体里持续出现佩戴虎头面具的主体。仔细观察,偶可通过他手握自拍定时器的线去辨认面具之下的摄影师本体,但当面具抹去了表情并重新赋予不同的角度,场景便变得模糊暧昧,其他没有佩戴面具的摄影对象正安然面对镜头或者自然地身处其中,这种割裂让人不得不在画中一再去追寻更多情感表达的蛛丝马迹。
并且试图去理解、感受作品所带来的、即将要倾泻而出的一切。
观看之道:凝视的方式
同样,肖像画并不仅仅在于揭露一种同一性(identité)或者一个“我”。也许,“我总是被寻找的。”...因而不再是复制,甚至不是展示,而是产生那个被外展的——主体(l' exposé-su-jet)。生——产(pro-duire)这个主体,把这个主体带到面前,把它引向外面。
——让-吕克·南希《肖像画的凝视》
我把我所认识的白川,分成了好几个人。
在水象第一期的采访《一个收藏古茶器的朋克》里,他是知名的时尚摄影师、收藏者;当爱米第一次带我到满是黑胶唱片的“老虎上树”,他是黑胶唱片收藏家;当老虎上树的一楼开始了器皿展览,他是艺术指导、策展人。
白川在《虎的迷途》开幕现场
而在这次的摄影展及这份摄影画册面前,我被迫把一切对白川的认知、交往时候的印象一一抛却,只是纯粹作为观看作品的人,重新去读取镜头之后的人。
每个摄影师都应该有他的定义,我们才得以可能从这小小缺口去窥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怎么看,怎么捕捉,怎么思考,所以我不得不问白川,“摄影究竟是什么?”
“你的这个命题太大了。”他思考了一下,抓到了一个词汇,“我觉得摄影是一种材料。像油画、雕塑,只是一种表达手段。”
在白川作为工作所创作的摄影和私人作品之间,(摄影作为)同一种材料,却是能自如切换在两者并完全不会相互影响。
在时尚摄影工作中,时装模特、明星、演员、台上的群像,是“技术的表达”,并且可以跟着时尚美学这套东西,见证这些年的变化。在某些工作上创造的时刻,白川会更具备主导权,因为“商业主导”,但作为纯摄影师的身份来说,他并不喜欢太强势,与拍摄对象更多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互为主体。
而在私人创作中,情绪的流动十分微妙,不可描述的情愫、拍摄者与被拍者(凝视的对象)之间,是一种即兴,也是一种相互探视的关系;而在“人”以外,环境的关联也十分大:“有部分照片的环境是自然产生的,但大部分只要把面具戴上,就可以很即兴地创作。所以在我最后挑选出这些照片的时候,其实是通过对情绪的识别和表达从而作为选取的参数。”
老虎的意象:面具下的时代与景观
“因为,摄影使本人像另外一个人一样出现了:身份意识扭曲了、分裂了。......面对镜头,我同时是,我自以为是的那个,我希望人家以为我是的那个,摄影师以为我是的那个人,摄影师用以展示其艺术才能的那个人。在想象中,照片(我想拍的那种照片)表现的是难以捉摸的一刻,在那一刻,实在来说既非主体亦非客体,毋宁说是个感到自己正在变成客体的主体....”
——罗兰巴特《明室》
无论是无名摄影集,还是在厦门三影堂展览里所呈现的,重新叙述、排列的《虎的迷途》,始终围绕着“虎的在场”为视觉的中心点展开叙述。虎头面具的在场行为成为了作品中的媒介、视觉焦点,从这个中心点探索蔓延。这个道具既成为摄影师链接时间、场景、摄影者与观看者的媒介,同时也成为这多维身份里的一种边界设立。
我们在一个家常的餐桌上聊起这一切的开始。
“就如一部恶俗的电视剧。”白川像是找到一个无比贴切的形容词般来回应这一切的开始:“最初拍摄这一切的契机也非常简单,在我的本命年也就是2010年开始,各式事情集中地发生了。你可以去看看姜文的电影《本命年》,说的就是大时代下一个人的命运——中国人就是有(本命年)这样的观念。”
多事之秋,压缩着各种的生老病死,大时代下人的命运轮转。照片所呈现的其实也非常简单,生老病死压缩了在这十二年里。“各种事情就很如常地发生了,老虎头从哪来的,我也都不太记得了。”
但习惯了随身携带,在不同的场域中即兴拿出来戴上或者给其他人戴上,成就了这十二年的照片选集。
“那可以说在这作品里,‘老虎’是在替你完成某个角色、身份、或者某种表达吗?”
“其实我觉得这更像自拍照,只是没有拍到自己的脸。但我觉得没有拍到脸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你如果叫我不戴面具去拍这些照片也是可以的。”(可以吗,如果不戴面具,就要让自己的表情、情感在胶卷上一览无遗,坦白得毫无回转之地。)我心想着这个问题,没有问出口。白川继续和我讨论照片:“自拍照在摄影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像(辛迪·雪曼(Cindy Sherman)一样,她也是自拍照,她自己会去演很多角色,妓女、明星或者演一个流浪汉也可,演的角色远远超过了她自己本身。”
我想起K之前和我探讨过:“老虎头可能指向的就是摄影师另外的一个自己,借由面具抽离出来第三者的身份去在场经历,强迫自己去面对但同时藏起来一部分真实的自己”——这个“虎”的迷途,是他还是其他的谁?
“有时候我会让其他人戴上头套去拍照,这个人就成为了我。戴上老虎头之后身份的边界模糊了,如果影像里有多于一个老虎,或者有十个老虎,那其实都是我。合影里‘老虎’与其他人发生了关系,也代表着作者本人。而我也会有无法按快门的时候,就会有其他人代替摄影的位置。但在画面中,从创作者到角色扮演者,到最后还是我自己。我,我和这个场景发生了关系,最后看起来就像一个舞台剧。”
关于“老虎头套”,白川觉得它“看似缺乏表情,但每一张对他来说都拥有丰富的表情。”
但在我看来,每一张照片里的“虎”因为角度、光照与阴影、随着场景的变换,充满张力和似言未语的姿势,正从照片中不断掳取人的视线和关注。明明是一模一样的物件(虎头面具),但它有了表情,这表情通过摄影的视觉与环境的表达,还有面具与周围不同的人合影后产生的关联,它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符号。
横在拍摄者与观众之间的这种对峙——罗兰巴特会说,“照片表现的是难以捉摸的一刻。”
“如果你看得再仔细,把照片再放大,你还可以看到那老虎的眼睛,识别到里面喜怒哀乐的眼神,里面还包括有很多快乐的、调侃的眼神,或者完全无意义的。我觉得,在观看的一百人里面,有一个人看到了它的表情,目的就达到了。” 白川又补充道。
哀痛日记:无可避免的日常纪事
有人说:时间会平息哀痛。——不,时间不会使任何东西消失;它只会使哀痛的情绪性消失。
——罗兰巴特《哀痛日记》
回顾照片中整个空间、时间的线索,变化的景观,重复但在变化中的人物和与观者情绪共鸣的无声但激烈撼动的观看体验,画面的本体取代了交流、倾诉,彷佛一旦形成文字,发出声音,便失去了某种力量的重击。
这是一次掏空情绪的无声交流,暗流涌动的单向读取式对话。我听取摄影师与观者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交叉叙述:
“他们看到什么,就是什么。”
“我哭了。看完一个人的12年,像看了场电影。”
“你的作品里记录的部分包括了对离别、死亡的悼念。”
“我觉得因为它自身的沉重会让其格外显眼和突出,但这并不是初衷,只能说在这人世生活的某个十二年里它出现了,又成为了个人体验里比较重的一部分,这可能换着任何人都无法避免。但它还是紧密地和其他日常生活参杂在一起的。”
这本命年到本命年的十二年里,不可回避的是这许多充满疑惑的、焦虑的、不安的部分,作为这系列作品的基调,它无法回避,不可减免。白川希望表达的部分,也不止离别或者面对生活沉重的部分,也有快乐和其他的情绪,有些荒诞但也有很多人情味在其中但它们彼此交错参杂,生活状态也好,生活压力也好,呈现出现在的这么一个结果。
“有一天朋友在看这本影集,看完和我说她哭了。”
“我并不想再去讲述关于照片—这也是照片的意义。有时候它十分私人,但当它呈现、铺开展示之后,观众看到什么,对我来说就不再重要了,它成为了一个作品。如果这个作品打动了其他人,对于作者来说肯定是挺开心的。”
“老虎以外的其他人呢,他们在现场又是怎么的一个情绪状态?”
“大部分人都是持一个开放的、好玩的、游戏的态度。拍摄一般我都提前会说明情况,一般都不会是临时起意。或者了解我的人知道我在创作。有些明星也是会有被吓到的场景—在工作结束后我们拍一个合照,我掏出老虎面具戴上的时刻。而陌生人或者公共场所我会提前去说,或者就算看到甚至有些街边的陌生人,比如在香港或者是在广州与路边的陌生人一起,我就说戴上这个能不能给你拍个合影,对方一般都觉得很有趣。我觉得大家还是有接受度的。”
最开始拍的时候,白川并没有什么宏大的想法,既没有想要做展览,更没有想要会持续拍了那么久,这里面可能最延续持久参与的就都是家人了。“家人因为对我的了解,在场景中都十分从容,不管是里面的喜怒哀乐,无论是否戴上面具。而我的父母更是从来不问,可能基于对我从小搞怪调皮的了解,就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
“你觉得这些场景的瞬间成为作品之后,是如实反映了当时,还是超出了你原来想要表达的?有了老虎这个中间的媒介之后,他的情绪表达会有不一样吗?”
“谈不上如实,我觉得照片本身就没有如实这一说。它是抽象的一个东西,一个物件,是观看者对他的感受。包括传统的所谓的纪实摄影,照片本身不可能如实的去表达一个东西,它是抽取出来、最后的成为是观看者对它的一个感受或者是作为创作者自己的一个感受。它无法定义或者给出一个一个准确的描述,但我觉得他一定不是如实地去表达——这不存在。我做摄影自己一直会有这个想法在里面,不管是拍这一组还是其他东西,都是这个看法对摄影个人的看法。”
“对看的人来说可能不一样,对我来说我觉得没有区别。我把没有选上的大部分照片扔掉了,在挑选的时候,有些会自我感觉动机不纯,比如我在美国、在冰岛,我可以拍出非常壮观的环境,在美感上它很美,但我把这部分都删掉了⋯⋯或者我戴了老虎头在冰岛的荒原上面,但是失去了拍摄的热情。我觉得这不是我想要的,只是单纯地成为了噱头。我宁可就在成都的家里面,或者是在很日常的很平常的视觉里面去拍摄。”
爱的定义:过往、当下与未来
如火焰般,记忆灼痛了我们,这带来的结果或好或坏:记忆使过去的事物重新处于生机勃勃而又紧迫万分的热度之中。或者,记忆会烧毁一切并让我们变得疯狂,如果我们不能将其能量转换为一种自由实践的话。
——迪迪-于贝尔曼《记忆的灼痛》
顺着摄影书中可见的叙述,从上一代的爱情,到对孩子的爱,到伴侣的爱,到整个家庭,除了作为在场的人,观看的人,摄影师更像一个主体,用记录的方式去表达这种“爱”的感情。
“我们这一代人的教育里并没有教会如何去表达爱。或者说对爱这个事情到底是什么并不是很清楚。这些作品其实可以作为对这个疑惑的一个提问,但非答案。我不停地在提问,通过老虎头、通过照片,但是没有定义。爱对我来说只能是一个问题,无法定义,也没有答案。“
“所以爱是什么?”
“让我翻一下书的最后一页。”
当白川把书翻至最后一页,当他说:“爱是什么,你就让这张照片作答即可。” 我便知道,就如知晓那本至今不能命名,没有一个字的摄影集,就是当下所有这一切,荣光、爱与死亡。
当文字、语言不能抵达,当深邃的哀不能诉之于任何外在,犹如诉之就会随风飘零而那一根细线从脊椎背后慢慢抽出痛及心扉的情感,需要用镜头、胶片,付着于时间,赋予力量并转化为“一种自由实践。”
“任何人都可以去对这照片做出解读,只要不太偏离目标即可?”
“我觉得他也可以偏离目标。”
每次与白川抽烟,总会被打断。天台上(他)的熟人、展览后的拜访与合照、女儿的一百道脑筋急转弯解题。而当我们正儿八经把烟...
作为次抛代工厂,韵斐诗是供应链上不可缺少的一环。多年来,韵斐诗一直持续专注于以条袋式、泡罩式、AFP立体铝箔式、面膜杯式...
【Fashion Talk】带你走入奢侈品与服饰行业的潮流前线。本期,下滑查看『Case 精选』长图,共同见证FILA网球裙如何缔造属于...
全球最大家族邮轮企业 MSC地中海邮轮以300年航海世家底蕴为宾客倾情打造船上私密专属空间——地中海游艇会,“船中船”概念...
蕉内携手品牌代言人王一博,为你的冬日带来“新皮肤”——第7代蕉内热皮保暖衣。全新第7代蕉内热皮,运用Airwarm空气锁温技术...
今年,Pt铂金携手《时尚新娘COSMOBride》,记录陈紫函和戴向宇互为底气、双向奔赴的爱情。陈紫函和戴向宇从公布恋情到步入婚...